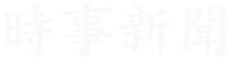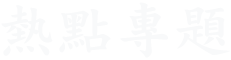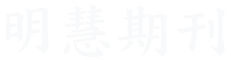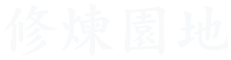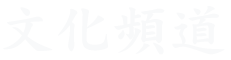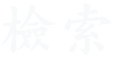心念正 神跡顯
當我剛獲得自由,回到母親家中,第一位見到我的人──昔日小學老師,不禁抱住我大哭。在這一年中,也有不少熟人、親人問我:「不覺得苦、不公平嗎?」
苦嗎?──我捫心自問──是,悟不明法理,無意中承認了舊勢力安排,沒有做到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狀態修煉,使親人和有緣人也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苦!
苦嗎?──在十年的正法歸路中,破除舊勢力讓我失去肉身的安排,破除被所謂「轉化」的邪惡安排──「慧者心自清,苦中樂長駐」。不苦!
苦嗎?──十年風雨征程中,當心在法上,堅定真修時,神跡處處顯現,時時感受師尊的慈悲呵護──幸福!
二零零零年在看守所,警察將我踩在地上,用又長又粗的管子灌了我一洗臉盆的液體,導致我吐血、高燒,全身淋巴起包塊,口腔食道潰爛流膿,看守所只得提前釋放。母親將我接回家,因連續多日被加戴戒具,我已無力坐起,我請母親放師父講法錄像,聽後入睡,次日早起所有症狀全部消失。母親不放心,晚上起來看我幾次,睡得很好,疑是夢中。類似事例,母親見證幾次。
二零零一年,我絕食七個多月被保外就醫時,省級部門諸官員找家人談話,一向膽小怕事的母親堂堂正正對他們說:「請回答我三個問題,我就簽字。1、我女兒從來未說過假話,你們每次說謊,是說真話好,還是說假話好?2、我女兒從沒恨過你們,還私下對我們說你們可憐,幹違背自己良心的事,你們這麼仇恨她們,說她們邪,一次又一次迫害,是善良的人邪,還是整人的人邪?3、中共提無神論,我也信科學,不信神,為啥子每次她都被你們整得要死了才放出來,一煉功就恢復了,甚至人都坐不起來了,聽一下她師父講話錄音就好了哪?我不敢信神,但請你們解釋一下,你們大官,比我這個老百姓有本事。」
官員們互相看看,都不說話,最後母親沒交一分錢,沒寫任何保證,將我從勞教所接出。一個月後,我的體重從60多斤恢復到100多斤,血壓從50恢復到正常,腎、心、肝功能衰竭恢復正常,醫生說這是醫學奇蹟,不打針吃藥,硬是煉功就好了。
後來三退開始時,母親選擇退出了邪黨的團、隊,她說:「現在我相信真的有神,不然你早死了不知多少回了。」
邪惡下藥不起作用
二零零一年,我曾在鄉醫院被四個小伙子按倒強行注射類似安定類藥物。我正告他們:「別來這一套,我是修煉人,不管用。」參與迫害的醫生說:「別管她,打完就鬆手,我數三聲她就倒。」他數了半天,我平靜地坐在那兒注視著他。
醫生奇怪地說:「怎麼不倒呢?」
「我是修煉人。」
旁邊的惡人問:「是否藥力不夠?」
「不,超大劑量,馬上就要睡過去。」
「過期了?」
「是新藥。」
「效果不好?」
「好藥,不信,這兒還有一點,你來試試?」
「哦,不、不。」
惡人們都走了,從此,醫生們再也沒有參與過迫害。
二零零七年,我在洗腦班被關了幾年,絕食抗議了幾年,期間惡人們給我灌生雞蛋,妄圖讓我拉脫水,送去醫院迫害,而我根本沒上廁所,最後他們搞不明白我為甚麼不拉肚子,跑來問我,我才知道他們的險惡用心。後來,他們又在灌飯時在飯中下藥,我發一念讓藥從另外空間排走,藥根本不起作用;又連續一個多月不給我灌食了,想渴死、餓死我,我只是每天默默的坐在那兒發正念,邪惡的伎倆也不起作用。最後所謂的「護監」害怕了,報告洗腦班頭目,不然她要回家了,不然「要餵飯就好好喂,不想幹這缺德事,負不起責任。」
「剿惡記」
二零零二年短暫的流離失所期間,我有緣參加了一些證實法的項目,在資料點待了七個月,當時環境邪惡干擾大,從買原材料、製作、運送、發放中也經歷種種,七個月的經歷簡直可寫一部「剿惡記」。
我不懂專業知識,花三百多元買了袋碳粉卻無法複印,經技術同修鑑定是偽劣產品。我雙盤坐下,心中求師父加持,對著碳粉發正念,發了整整半個小時,一試成功。那袋粉用了很久,超過優質粉的使用期。
二零零零年冬天,我往藏區送資料,招手上車一看,坐滿了藏民,我和同行的同修是車上僅有的兩個漢人。
一個邪裏邪氣的藏族男子靠近我身邊,一旁的藏族老阿媽示意我小心口袋裏的錢,我放進了手套。一會兒,他又湊過來,嘴裏哼著歌,將手搭在我的腰上,我不是很怕。但想我是修煉人,應該忍?還是……對,我是大法弟子,如任由他被邪惡支撐著撒野,也會害了他。我默念著「正一切不正的」(《北京國際交流會講法》)轉過身面對他,眼光投向窗外。我感到全身放出萬道金光。這時突然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那男子「啊」的大叫一聲,倒退了幾步,身子向後倒下。我慢慢將眼光收回,盯著他的眼睛,他好像看到了甚麼,眼中露出害怕、祈求的光,又大叫了一聲,哆嗦著不敢動。這時我覺得自己身體變得萬丈高,就像一尊雪山女神。過了一分鐘,我將眼光又投向窗外,他才爬起來,連滾帶爬回到最後一排,再也沒敢過來了。滿車的藏民驚愕的注視著這一切,旁邊的藏民夫婦熱情的和我打招呼,請我吃東西,我也笑著與他們攀談。
二零零二年春天,我們已換上了麻紗春裝,沒想到藏區春寒料峭,還在下鵝毛大雪,地上堆著厚厚的積雪,那兒的人們穿著厚厚的冬裝,我們卻一點兒也不覺得冷,連當地功友拿的毛衣也用不著穿。當時四輛客車同行,我們乘坐的那輛開在前,可途中遇到前面車禍中疏散乘客,這輛車超載了很多,漸漸落在了最後。在距目地地一百多公里時,我發現同修大姐進入昏睡狀態,叫不醒。我腦中突然出現一念:前面有危險,快發正念。於是,我一刻不停的發正念,累了,休息一會兒,又發。
草原上的路,一眼望去可以看很遠,我發現將去的縣城方向陰雲密布。漸漸的,烏雲淡了,散了。當車子還有十幾公里就到時,烏雲四散,一輪金光閃閃的太陽跳了出來。這時,我看到,這條藏區與外界唯一的通道兩邊,布滿了軍隊、警察、武警、國安、民兵等,所有的車被攔截了下來,在路邊等待,每個乘客被勒令排隊接受檢查。後來得知同修在縣城及周圍發了許多真相資料,邪惡調集了大量人力包圍了車站、旅店、交通要道,專查大法資料。這時,我全心在正念中,心中沒有一絲擔心與揣測應該怎麼對付他們,根本沒有想與我有甚麼相干,只想著快點進站、下貨、找人。沒有誰來攔截,我們的客車直接開進了路邊的車站。我推醒大姐,帶著兩大包資料下車,一輛三輪過來,坐上去,剛出站,惡人們湧進了客站。
到旅店後,我將所有的資料裝進一個口袋背上,決定趁黑獨自去給功友送資料,大姐在旅店發正念。我坐在三輪車上,三輪車夫向前蹬著蹬著,突然停下,我納悶了:「不走了?」他嚇得聲音變了調:「狗,一條大藏狗。」我定睛一看,一個黑茸茸的東西蹲在三輪車前。草地上的藏狗像狼一般大小,可以咬死人的。我從小怕狗,此時卻平靜的站起來,一手指著它,說道:「孽障,還不快快退下,休得驚擾路人。」感覺自己像古人說話一樣。狗倒退著,掉頭跑了。我轉身一看,哦,原來走過了,前面是草原了。我叫車夫回轉頭,下車後,多給了他一塊錢,說:「你受驚了,多給你一塊錢。」車夫仍然驚魂未定的看著車後,唯恐狗跟過來,我安慰他:「沒事兒,它不會再來了,你儘管放心去吧。」車夫回過神來,非要把錢還給我:「不,大姐,說多少就是多少,不敢多要,謝謝你。」他用詫異和敬佩的眼光看著我,然後飛快的蹬起三輪沒命的跑了。
我敲響了門,同修起了床。突然,我覺得腿後有甚麼動靜,回頭一看,好傢伙,他家那條兇猛的藏狗此時正蹲在我的腿邊,靜悄悄的看著我,乖乖的像個孩子。要知道,這傢伙只認他的男、女主人,連家中其他人都要咬。我一樂,笑著:「你這畜生,倒也懂事,知道我是誰,來幹甚麼,不叫呀。」狗兒仰著頭,臉上露出興奮的表情,眼神激動,尾巴搖得快斷了。功友一把將我拉進屋:「好險啊,今天守的人剛走,你早來一會兒就麻煩了。」我心中忽然哽咽起來:「師父啊!」
十年來,從生活的大都市到山區、草原,從鄉村到周邊縣城,到北京上訪,從派出所、看守所、勞教所、監獄到賓館黑窩、邪惡的洗腦班,我用正念闖過了一關又一關,一次次化解了邪惡企圖暴打、酷刑、餓飯、灌食等折磨,歷經數次腎衰竭病危、疥瘡等險情,正念癒合了被打裂的傷口,善解了歷史上輪迴轉生中的冤怨──特別是在洗腦班,那個人間地獄。跟著師尊,我一次次地闖了過來,用正念破除了舊勢力的一切邪惡安排。我不能再讓邪惡把我釘在十字架上了,因為我是大法弟子。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2/8/20/1350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