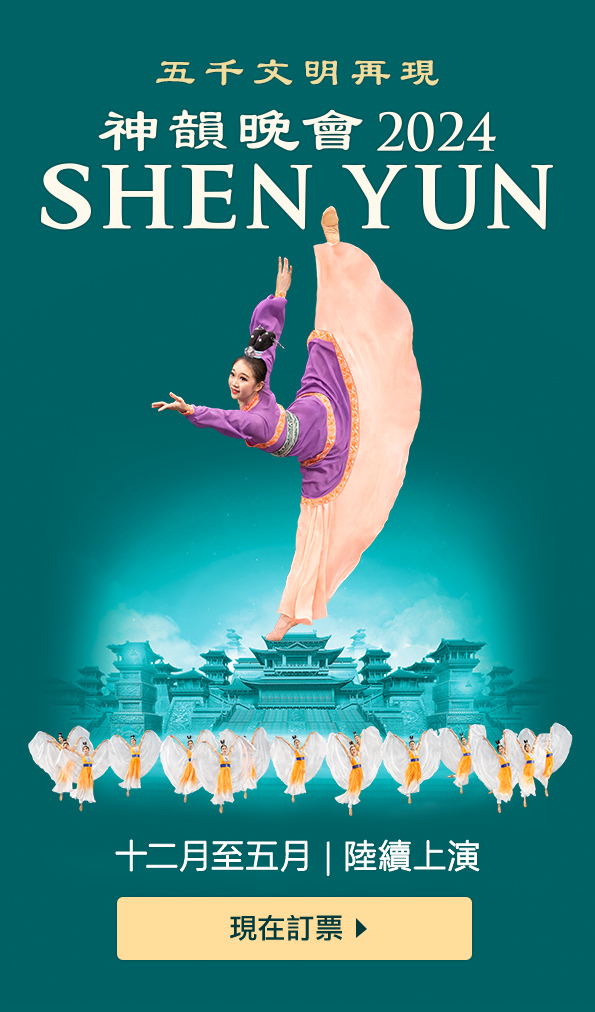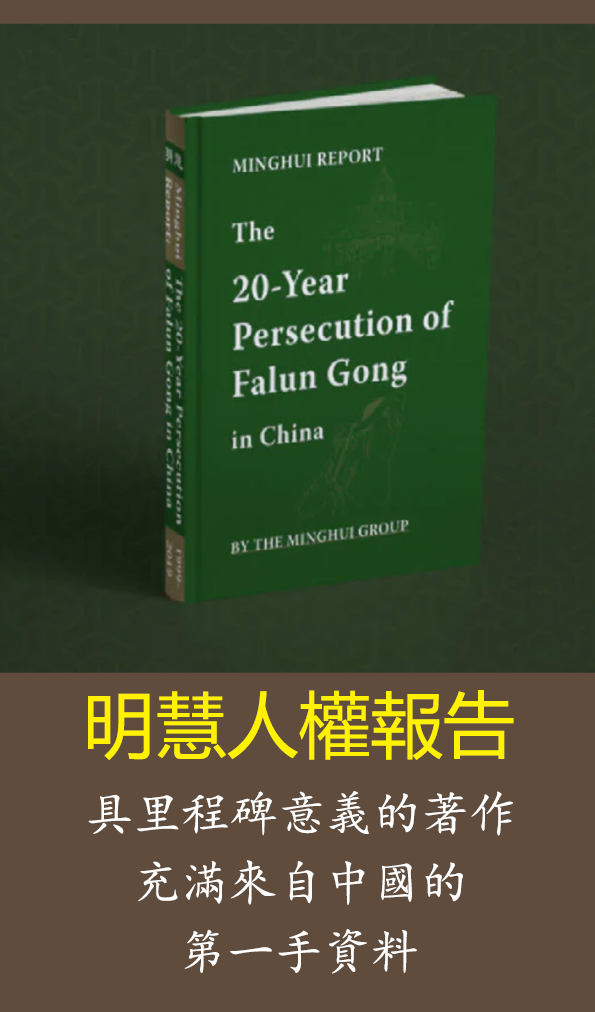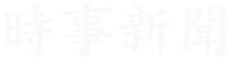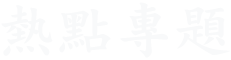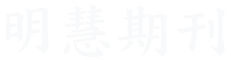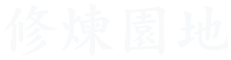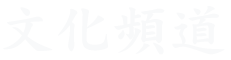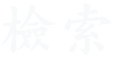外科醫生為講真話遭受的牢獄折磨
1995年6月我工作調轉到了大連市某醫院,我仍然堅持每天煉功,後來我又找到了就近煉功點,參加集體學法煉功。按照大法的要求,我到大連工作後不再收紅包,不再參加患者請客,受到了醫患一致好評。
1999年7.20一夜之間,有法輪功學員無故被抓,我和大家一起去信訪辦要人,被警察暴力驅散。地方政府解決不了問題,不能公開煉功。惡人對大法的誣陷越來越加碼,我的心裏別提多難受了。我要主持公道,我要對大法負責,可是去上訪意味著現有利益可能會失去,我為之奮鬥獲得的一切可能會失去,但是我再也不能等待了,我決定去北京為師父為大法討還公道。我與母親說了我的想法,母親也要去把自己學法煉功受益的情況向有關部門反映。就這樣,經過一番準備,我們三代人:母親、我及22個月大的外甥女,於2000年2月29日由大連乘飛機直抵北京,下飛機已是下午2點多了,乘汽車到市內已接近4點鐘。信訪辦在哪也找不到,我們就直奔天安門廣場,在國旗桿與紀念碑之間正中位置,我們面向天安門,開始煉第二套功法──法輪樁法。不一會兒一群警察圍了上來,問我們在幹甚麼?我們告訴他們在煉功,「煉甚麼功?」「法輪功。」他們把我們推上一輛依維柯汽車,送到了天安門廣場派出所,登記後又被關進了鐵籠子裏,那裏已經關了上百名各地來京的大法弟子。
大家在一起交流,都認識到走出來晚了,讓惡人如此橫行。但我高興自己到底走了出來,認識到應該站出來證實法。後來有一個年輕女學員帶著一本書被惡警發現了,問她帶的是甚麼書,她說是《轉法輪》,當惡警得到證實後,就往鐵籠裏衝,我站在鐵籠口阻擋他衝進來,被他一陣連串拳腳打得眼冒金星,幸好被其他大法弟子扶住。那個女學員也被打倒在地被拖出了鐵籠子。我們在一起背《論語》、《洪吟》震懾邪惡。不一會兒大連駐京辦事處的警察把我們接到了他們的辦公地點,記得是建新賓館十六樓。帶頭的叫王國慶,他們非法搜身,搜去了我的身份證,至今仍未歸還。
由於我被打,兩眼瞼處瘀血,像戴了墨鏡一樣,因此沒有馬上把我們送回大連,在賓館裏關了三天才往回送。到大連後被非法關進了台山村淨水廠附近的司法局戒毒所三樓,當天我的小外甥女被接出去。6天後片警逼我爸爸交了3000元錢把媽媽接走了,後來又被送姚家看守所關押,並要關押費200元。
我在戒毒所裡感到了寂寞,感到了不能學法的痛苦。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在一起切磋,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們晚上煉功,後來我們得到了一本《轉法輪》,我們晚上輪流學,每人一講,藉著走廊透進屋內的燈光學,這次學法和以往完全不一樣,學了一遍之後,覺得自己信心百倍,知道應該堅決抵制迫害。後來我堅決拒絕看惡警給的誣蔑大法的材料,又被惡警用拖鞋打了耳光,但我堅決不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天惡警又組織洗腦,我堅決不參加,被關進了二樓的禁閉室,禁區閉室地上有個鐵環,手銬穿過鐵環,我的雙手被銬住,人也就被釘住在地上。後來單位裏的書記蔣×、保衛科長矍××、派出所張副所長把我爸爸找來,逼著交了4000元錢,戒毒所才放人。在大連市司法局戒毒所,我被非法關押了23天,然後又被送進了姚空看守所,並被要去了200元關押費。15天後派出所張副所長、單位的書記蔣××和黨辦主任宋××一起來到看守所,問我還煉不煉了,我說煉。他們就又把我送回戒毒所,戒毒所的人說甚麼也不收。他們就把我帶回了單位。
從此我失去了臨床工作,被安排去掃廁所、拖病房走廊地面,每月只給270元生活費。後來醫院幹部蔣×要求我寫「保證」,不然就送教養院,並把610的人和教養院的人都找來了,在這種形勢下,我違心地寫了不煉功的保證。此後我就像失去了主心骨一樣,即便數月後因工作需要我又恢復了臨床工作,但每天的生活卻是極其壓抑和痛苦的。為了改變這一切,我要繼續學法煉功,並上網聲明所謂「保證」作廢,我決定再次上訪。這次為了不影響到其他人,即使是書記、院長,我也不能讓他們因我受到傷害,為此我寫了辭職申請,辭去在醫院的工作。
我於2001年2月27日晚又坐火車,於2月28日清晨到北京,坐地鐵到天安門廣場,從地鐵門一上到廣場我就打開了黃色橫幅,上面寫著「還李大師清白」,並高呼「還大法清白」、「還李大師清白」、「法輪大法是正法」等。從地鐵東門向天安門走去,快到英雄紀念碑處時,一個便衣警察衝過來了,我躲開了他,在廣場上奔跑,不讓他捉住,可是另一個便衣堵住了我的去路一群武警圍上來,把我抬進了依維柯汽車,又拖到了天安門廣場派出所。
在派出所裏,執班警察問我叫甚麼名字,從哪裏來,我全不告訴他。他又要把我銬到暖氣管子上,我堅決不順從他,還趁機跑出了派出所,被外面的警察又抓了回去。這過程中他們用警棍猛擊我的頭部。
他們把我帶到了一個房間裏,裏面有五、六個穿制服的警察,但都不戴警號,有一個警察在我面前一晃,接著一拳打在我的右眼處,我後仰倒了下去。他們一擁而上,把我按倒在地,給我上蘇秦背劍式的背銬,(就是右手從肩上背過,左手從腰間背過,兩隻手斜著在背後銬在一起),接著扒下我的褲子露出臀部。有人踩住了我的後背,有人按住了我的雙腿,一陣雨點般的警棍落在我身上,刀割般的疼痛鑽心,我幾乎忍不住了,一想起師父就在看著呢,絕不能跌倒,我心裏一橫,咬緊牙關,心裏背著《正大穹》──「邪惡逞幾時 盡顯眾生志 此劫誰在外 笑看眾神癡」,痛感越來越輕,後來我就甚麼都不知道了,有人用涼水激醒了我,接著有人用電棍來電我,又用棉籤蘸上一種很刺激的藥水塗在我的頸部和鼻孔裏,又有人在臀部踩來踩去;又有人用警棍在我的大腿後側及臀部碾來碾去。我幾次失去知覺,但從沒出一聲。
他們打累了,就把我抬到有大鐵籠那個房間,關在鐵籠子裏,鎖在鐵椅子上。我心裏明白,可身上一點力氣也沒有,我的全身被汗水浸透,有人問我喝不喝水,我已經沒有力氣吱聲。大約每過一小時就有人來觀察我的情況,見我沒出有任何反應,他們抬起我的腿把我的腳提得高高的,把腳後跟摔在水泥地上,我一點痛感也沒有。警察打電話說:「我們這裏出了一個截癱的,快派人來看看。」
到中午有時候,我趁他們吃飯時走出了鐵籠,當我要走出派出所的時候又被抓了回來。我俯臥在長條凳上一下午。警察幾次來詐我說:「你是某某某,別裝了,快認了吧,有人來領你回家了,起來吧。」每次他們都換名字試探。多個地方駐京機構來人認人,都沒有認出我是誰。甚至惡警與某地一個駐京機構的人都說好了,就把我當作某某某帶走。那人走近了我,看到了我的眼部血腫,就說甚麼也不肯把我帶走了。我臀部的傷更重,已被褲子蓋住了。
大約一直到晚上9點多鐘,我就起來了,有負責的警察要我給他拖地,我就坐在地上,後來他把我送出了派出所,還說:我今天差點兒攤事兒。你還來不來北京了?你說吧,從哪裏來的?我甚麼也沒回答他。他把我放到路邊就走了。我想返回天安門廣場,沒有走多遠,那個警察又回來了(可能是派出所旁的食雜攤打電話告訴了警察,因我向他們打聽天安門在哪),不讓我往回走,我只好往火車站方向走,這方向沒有公交車。我走進一家食雜店,想買點吃的,可一陣頭暈我就甚麼都不知道了,醒來時,我已被帶進了另一個派出所,關在看守間裏。在那裏我喝了一點水,頭腦清醒了許多。我想我得出去就要求他們放了我,他們非要我說出從哪來的才行,我沒有告訴他們,告訴他們我遭劫匪了。他們仍不放我。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就喊頭痛,要去醫院,他們問:「你有錢嗎?」「沒錢也得看,我受不了了。」執班的人說請示所長後再說,過了一會兒他回來說,你自己去看病吧。就把我給放了。
出來後,我走到了火車站,已是半夜,沒有火車了,只有汽車,有到大連和瀋陽的,我就搭車到了瀋陽。3月1日坐火車回到了大連家中。
家裏人看到我嚇了一跳,我右眼處一個大血腫,臀部及雙側股後部全都是血腫。經過近一個月的休養才康復。
2001年4月22日我在人民廣場講真象,被惡人舉報,被抓到了人民廣場派出所,當晚我被刑訊逼供,全身被潑涼水後在風中凍。4月23日晨我從手銬抽出手,堂堂正正離開了派出所。
2001年5月,惡警闖入我的家又把我抓到了派出所,他們不讓我穿鞋把我鎖在鐵椅子上,椅子上倒水不讓我坐,不讓我睡覺。我絕食抵制迫害。趙×還逼我妻子與我離婚,拿走我50元錢一套外衣及皮鞋、手機和傳呼機。我絕食一天半後,被送到了姚家看守所,經過53天關押後又被送到大連教養院,我不簽字,他們硬是把我塞進了教養院。
我堅決抵制「轉化」,並給邪悟者講真象,又被送到關山子教養院。在關山子教養院,我堅持煉功,絕食抗爭,抵制灌食、打點滴,終於獲得了煉功的權利。最後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魔窟。
我所遭受的迫害,只是千千萬萬法輪功修煉者的一個縮影。江××集團構陷迫害法輪大法,天理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