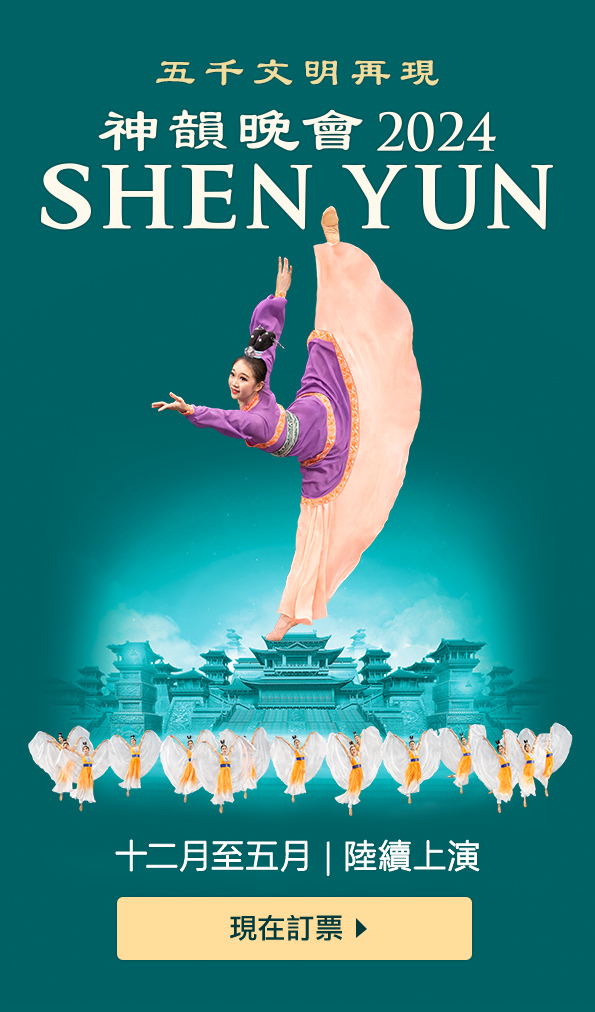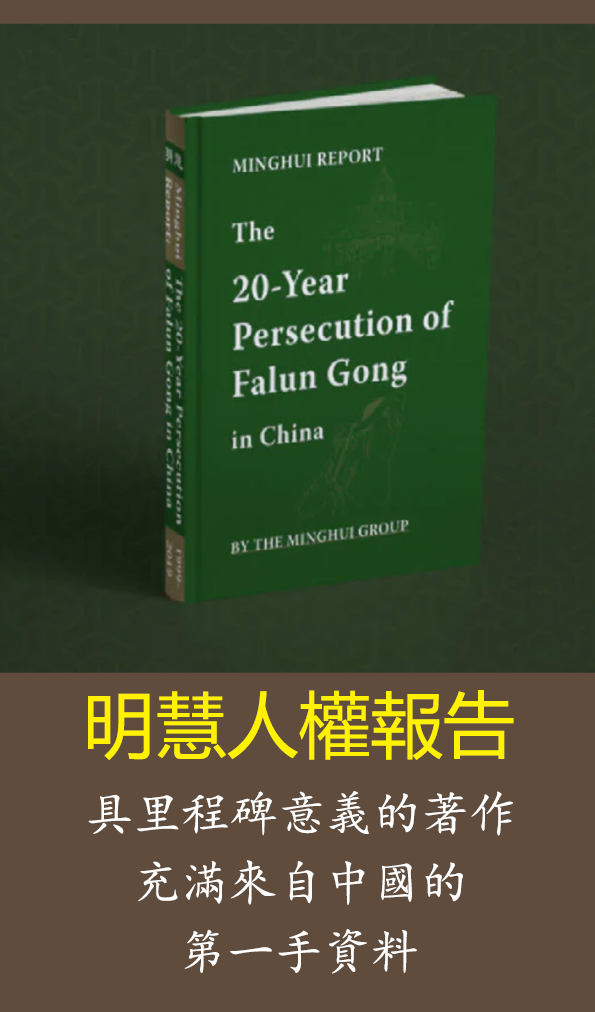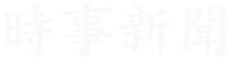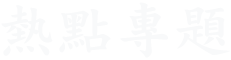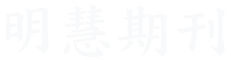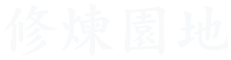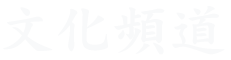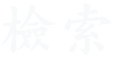大連市叢丕晶女士遭受的凶殘迫害
叢丕晶女士說,「我在禁閉室裏被非法關了六天,記得那時已是臘月二十五、六了,回到號裏,我的腿雖然漸漸消腫了,但卻鑽心地疼,兩隻腳都不敢落地,那幾天幾乎都是爬著走的。直到現在我的後腳筋有時還發麻。」
「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在我腰椎骨折的情況下,三次被綁架,如果不是大法的神威,我可能早是個廢人了,而這其中的神奇與痛苦也是一個常人所無法想像和做到的。在後來的日子裏,……也沒地方住,我拖著幾乎不能走路的身體流浪在大街上,還得躲避警察的盤查,晚上便露宿街頭,……現在想起來,都不寒而慄。」
江澤民發起這場凶殘迫害,使千千萬萬家庭遭受生離死別的痛苦,這場有系統的、大規模的恐怖迫害,及對大量善良法輪功學員的殺戮已持續近十七年了,懇請各界人士能發出正義之聲,幫助停止這場迫害。
以下部份是叢丕晶女士訴述她自九九年開始遭受的迫害:
第一次:自九九年四月份,迫害的苗頭就顯露了,那時我修煉法輪功時間短,只知道大法好,對於政府的做法並沒有太多的想法。七月份,市裏開始抓所謂的負責人,我知道這是不合理的,大法也沒甚麼負責人,只是你想學有人就教教怎麼煉,告訴你在哪兒買書,也沒甚麼組織。出於正義,我到市信訪辦,想把我的想法告訴他們,當時的人比較多,政府當時就出人鎮壓了,滿街都是武警,我們被塞進一個大公交車裏,也不知被拉到哪裏,好像是郊外的一個荒區。
第二天好不容易找到來路,剛到市政,就又被抓捕,我們連夜被送到一個學校裏,被關押了一宿,沒吃沒喝的,也不讓給外界打電話,警察都板著臉孔,很恐怖的,人生第一次感到我曾經最愛的國家竟然也有這樣恐怖的事情發生,我意識到事情並非想想的那樣簡單,第三天,我們被放走,告訴回家看新聞。
從那時起,席捲全國的迫害就開始了。
第二次:以親身經歷,我知道大法好,大法真的很超常。為了討回公道,九九年十月我去北京上訪,在天安門廣場被警察劫持到豐台體育場,後被非法關押到北京密雲看守所,這個看守所裏的警察非常殘暴(明慧網曾有過多次報導。那裏的警察遭報死的也有不少),他們利用各種酷刑、體罰折磨大法弟子,強迫我們說出姓名和住址。當時我們絕食抗議,被強行灌食,他們口口聲聲說:保證說了姓名和地址送回去就沒事了。一些大法弟子報了姓名和地址,陸陸續續都被帶走了。
最後我也被迫報了姓名和地址,之後被挾持回當地看守所,當時說是拘留,可是一呆就是半年,在這六個月的非法關押期間,我在看守所裏遭到了種種非人的待遇,為了爭取煉功環境,經常遭到管教的謾罵、恐嚇、侮辱。當時的女所長是管秀娟有一次說是上面來檢查,不讓我們煉功,我們集體絕食抗議,之後我們被關進禁閉室。
當時已是臘月的天氣了,天特別冷,禁閉室裏陰森森的,聽說這裏還從來沒有關過女的,法輪功學員還是先例,警察把我們手腳都銬在鐵椅上,動彈不了,白天晚上都這樣坐著,不讓我們睡覺,沒過兩天,我的手腳腫得像個大饅頭似的,鐵鐐子都深深地摳進肉裏去了,有的同修滿腳、腳脖子都起了大血泡,疼痛難忍。特別到了晚上,又冷又癢,整夜都無法閤眼。有一天晚上,我的身體反應得特別厲害,感覺上是發冷,凍得直哆嗦,而實際上是在發高燒,照看我們的刑事大姐用手摸摸我的腳鐐,說腳鐐子都燙手,她當時都哭了。
 雙手銬在椅子上 |
我在禁閉室裏被非法關了六天,記得那時已是臘月二十五、六了,回到號裏,我的腿雖然漸漸消腫了,但卻鑽心地疼,兩隻腳都不敢落地,那幾天幾乎都是爬著走的。直到現在我的後腳筋有時還發麻。
我認為這裏不是我應該呆的地方,我不能在這裏消極承受警察對我的迫害,過了幾天,我的雙腳慢慢敢走路了,我就又開始煉功。結果我又被拖出去上刑。(記得那時是二零零零年元月初十)他們把我的手腳銬在一個像「井」字形的刑具上,刑具的底部和牆上的鐵環鎖在一起,把我鎖在牆邊,頭只能朝下,使你想蹲蹲不下,欲站站不起,這種刑具據說常人上去幾分鐘就得暈過去。警察還在走廊裏來回走動,嘲笑我說「這回看你還煉不煉功了,這樣比煉功好多了,一會兒就讓你過去(意思就是暈過去)。」
他們把我銬了一個多小時後把我放下來。為了不讓我們煉功,把我們幾個同修的手和腳全連在一起,靠牆邊坐成一排,晚上也不讓我們躺著,上廁所都得九個人一起去,因為手和腳都被連在一起,行動極不方便。為了抵制迫害,我們又一起背法,結果又是被一頓毒打。警察唆使犯人(從男號裏放過來的打手)用膠皮棒抽打我們,用裝水的可樂瓶砸我們的頭,唆使女犯用涼水潑我們,一盆盆的冷水把我們從頭頂澆到腳底,渾身上下全濕透了,我的耳朵裏當時被灌得都聽不到聲音了。後來不知哪個男警察看不過眼了,直喊:「行了,行了,這是幹甚麼!」這時抽打聲、罵聲、喊叫聲、潑水聲才漸漸緩下來。
 中共酷刑示意圖:澆涼水 |
當時我哭了,為這些無知的生命而嘆息。這樣他們一直把我們銬到正月十五才放回號裏,回到號裏後,那個號長痛哭流涕,直向我們道歉(因她潑水潑得最多),口口聲聲說對不住我們,說她知道,說不定那一天她會因此而遭報(因為剛進來時是大法弟子最照顧她,她也看過大法書),她說她是被迫的,她只是想好好表現,想爭取早點放回家。
我出獄後,官方還經常派人到我家騷擾,使家人整天為我提心吊膽的,我父親長年有病(腦血栓後遺症)他們每次去,他就嚇得直哭,給他的身心健康帶來很大的壓力。
第三次: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一個剛搬家的房子裏,我又一次被綁架,當時由於他們搜出了我的身份證件,把我送到當地刑警大隊,有個惡警凶狠狠地對我說:「你可真行啊,這回非勞教你不可。」他們不讓我睡覺,連夜審我,對我大呼小叫的,我甚麼也沒說,他們對我軟硬兼施,一看沒戲了,一個惡警氣急敗壞地衝著我喊:「不說是不是?不給你點厲害你是不能說,看明天怎麼收拾你!」當時我很害怕,因為和我一起被抓的同修在正念下走脫了(註﹕這個同修叫李忠民,多次被抓,後來在監獄裏被活活打死,明慧多次報導過),就剩我一個了。當時搜出挺多做資料用的設備和原材料,後來聽說被列為東北大案,他們當時都像瘋了一樣。第二天,他們又對我輪番轟炸,體罰我,恐嚇我:「不說慢慢折磨你,整你有的是辦法。」
在刑警大隊,我不承受警察對我的迫害,趁他們不在時,我從窗戶跳下想走脫,但不幸受傷,當時我只是感覺腿有點麻,沒能及時走脫,被警察發現,他們把我拖回去,對我一陣毒打,我就再也起不來了。我躺在地上,有一陣子我甚麼都不知道了,好像是昏過去了,後來我知道是他們用水把我澆過來的。一下午他們就不停地折磨我,我不停地大叫,因為他們每動我一下,我的後背就沒命地疼(當時我不知道骨折了)。
直到晚上七、八點鐘的樣子,忽然進來一大幫人,把整人的傢伙都拿來了,看來是要對我大打出手了,那時我也不知道害怕了,已經豁出去了。可是沒一會兒,他們又都被叫出去了,一會兒又回來了,說是要帶我去醫院,當時我已經不能走路了,他們幾乎是把我從二樓連拖帶架下去的。他們把我帶到市中醫院,拍片後,醫生說我腰椎骨折,情況嚴重,必須住院,護理不好,可能會導致下身癱瘓。
當時我的左腿已經沒有任何知覺了,也沒有任何承負能力了,一動也不能動。他們把我放在急診室裏觀察了兩天,就把我抬到了看守所。當時由於僥倖心理,聽信了刑警的欺騙,他們說就你這樣看守所根本就不能收你,別說是煉法輪功,就是殺人犯也得先救人,後處理。可萬萬沒想到惡人竟然把我又送回看守所,我當時已經不能動彈了,連翻身都翻不了。
進看守所後,他們仍然折磨我,把我自己單獨放在一個空屋子裏,對我採用車輪戰術,連審了我四天四夜,晚上也不讓我睡覺,我一閉眼他們就用礦泉水瓶砸板鋪,砸得銧銧直響。有一個惡警竟然氣急敗壞地用礦泉水瓶砸我的胳膊,不准我閉眼。有一個年輕的惡警特別邪,聽說是剛畢業不久的,是從別處調來幫忙的,他不讓我閉眼,不讓我出聲,以至於警察不讓我小便(因為我當時動彈不了,得讓號裏負責照看我那幾個刑事犯幫我),我幾次告訴他,他都不給我找人幫忙,還說:「你不是能忍嗎?你就忍著吧!」
我開始絕食抗議這種沒有法律、沒有人權的摧殘。他們強行給我灌食,每次灌食,我都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因為我的腰部根本就不敢動,灌食時,我一咳嗽、嘔吐的時候腰就跟著劇烈的疼痛。我強忍著疼痛,就是不配合他們,後來幾次,他們也許怕出事,把我送去醫院灌食,抬不動,他們就把我放到地上,用棉被拖著走,每到醫院折騰一次,我的全身就像散了架一樣,疼痛難忍。
後來我的左腿肌肉萎縮的特別厲害,他們強行給我打點滴,用四、五個人把著我,我盡力抵制,絕食二十八天,人已經瘦得不像樣了,他們可能怕擔責任,才臨時通知我的家人把我秘密接回家。當時連我都不知道,我的家人也是當天接到電話才知道的,在我被抓後他們並沒依法律程序及時通知我的家人。在這期間,我要求見家人,他們不讓,我想要換洗的內衣,他們也不給拿,當時我穿的褲頭都是號裏的犯人穿過不要的。
回家後,他們還總派人去騷擾,而且他們還告訴我,事還沒完(那就意味著等我的家人把我的身體照顧好之後,他們會隨時把我帶走)整得家裏一時都不得安寧,我父親一看他們來,就嚇得嗚嗚直哭,我不忍心再為這個家添麻煩了,本來我媽伺候我爸一個人,家裏負擔已經夠重的,再讓我媽(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為我端屎接尿的,誰還能忍心呢?!
我決定離家出走,可我又動彈不了,但憑著對師父、對法的正信,我堅信我一定能走。我開始打起精神,躺在炕上不停地發正念,求師父加持我。沒過幾天,我奇蹟般地站起來了。後來,在師父的呵護下,我離開了家。
第四次:二零零一年八月,在離家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裏,我在一個同修的住處養傷,因那位同修去菜市買東西被跟蹤到家,我又一次遭受非人的折磨。當時,我在屋裏聽到門外同修和他們的撕扯聲,我知道出事了,我想我不能這樣等著被帶走,我要喊人,揭露他們的卑鄙行為,我使出渾身的力氣,好不容易才爬上窗台,剛扶著窗台站穩,門外的警察已經衝進來了,急忙中我就開喊;「不許過來!快來人哪,警察抓好人了。」那個惡警也許發現情況不妙,沒過來。
當時我不停地喊,樓下的老百姓越來越多,由於身體的不便,我無法走脫,我就開始向他們講真相。沒過幾分鐘,來了三、四台警車,還有消防車,旁邊還有人在錄像,我當時就揭穿他們的陰謀,他們又要製造跳樓自殺現場。我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戒,不停地給老百姓講真相,警察想把我騙回屋裏,我告訴他們警力不退我是不會回去的,我要讓老百姓知道你們是怎樣迫害大法弟子的。僵持大約有一個半多小時,趁我不注意,一個消防隊員從屋裏衝出來,一把拽住了我,我往後一晃,一隻腳滑下去了,剎那間,他用力一甩手,把我從二樓推下去了。
下面的惡警用腳狠狠地踩著我,當時地上不知從哪兒來的水,弄得我滿身都是泥巴,據當時目擊者說,我當時已經被整得不像人樣了(光著腳,穿了一個舊汗衫,一條室內穿的短褲),已經看不見模樣了。當時我已是迷昏過去了,後來身體劇烈的疼痛,使我又甦醒過來了,他們把我抬上警車,我不停的喊:「法輪大法好!」他們就掐我的脖子,捂我的嘴,還不停地罵我,威脅我。
 酷刑演示:綁在鐵椅子上電擊 |
後來我被帶到派出所,他們把我銬在鐵椅上,剛剛好點的身體,根本就經不起這般摧殘,他們用電棍電我,聽說好像是二千伏的電壓,穿著鞋踹我的臉和嘴,不讓我喊,我身上好多處都被電糊了,後來他們把我拖到一個黑屋子裏,開始打我,沒過多久,外面進來的人說要帶我去醫院檢查。
檢查結果說是腰椎骨折,即使這樣,警察還是把我的手腳分別銬在床頭上,我動彈不了,只能一個姿勢躺著。他們給我打點滴,我堅決抵制,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打的是甚麼,在當時有些同修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當成了實驗品。我無法出去大小便,他們強行給我插導尿管,這給我的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壓力,以至於後來我被迫害得小便失禁。我絕食抗議,第二天晚上,他們把我送到住院部,我拒絕配合他們的任何要求。第三天他們不得不放人。
惡警侵吞了我們一千一百多塊錢(後來同修跟他們要,居然說讓我住院花了,我只是在醫院呆了三宿,沒吃沒喝,也沒打針,竟然花掉這麼多錢,簡直是荒唐。)兩部手機,一個傳呼,還有大法書籍,家裏還有同修給拿來的好一點的窗簾、毛巾都被劫持而空,還有同修給我買的一雙新涼鞋,打算等我能走路時好穿著,也都不知去向了。
第五次:二零零一年九月上旬,我被迫到另一同修家養傷,可沒過幾天,那位同修因發真相資料被舉報,我又一次被綁架,惡警去砸門,那個同修沒給開,結果警察從鄰居屋裏進入,砸碎玻璃,破窗而入,把那個大法弟子毒打一頓後,又把我和另一個同修一起拖上了警車。
當時被抓的有三個同修,警察把我們帶到了派出所,強行給我們拍照,之後,把我們送到了區分局,把我們三個分開非法關押,我們絕食抗議。當時我們三個人的身體狀況都不太好,一個同修被迫害心臟病復發,躺在屋裏動不了,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他們也不管。另一個大姐本來身體就不太好,加上被恐嚇、絕食,渾身發軟。我被拖拽得渾身都疼,躺在地鋪上動不了,加上小便失禁,更加劇了精神上的摧殘,我不停地哭喊著,警察就是不讓同修過來幫我,他們怕我們傳所謂的「口供」,這樣我就一直躺在尿窩裏,這對於我一個年輕的生命來說,無疑是一個無形的摧殘與侮辱。後來,他們竟把門窗全打開了,當時我只穿了一件汗衫和一條大短褲,全都是濕的,風刮進來,我凍得直哆嗦……我無法找到更確切的語言來說出那段時間對我的身心的摧殘,直到現在想起來都無法平靜下來,心理的摧殘遠遠大於身體的承受。
第三天他們用警車把我們帶回租房處,把我們扔在樓下開車就跑了,只留下幾個便衣在監視我們。當時出來許多圍觀的老百姓,我就給他們講真相,警察可能怕暴露真相,一會兒又來了一些人,把我們全抬到樓上,我們心裏很清楚,他們並沒有放我們,只是在使花招,他們是想看我們跟誰聯繫,好蹲坑抓人。果然不出所料,晚上的時候,樓前樓後全是盯梢的。後來他們自己說漏了這事,以為我們是假裝的,如果下樓一個就抓一個,他們還派房東、鄰居不斷來試探我們。
呆到第四天,他們又把我們全帶到醫院去檢查,我不知道是哪家醫院,檢查後又把我們全塞進警車,一整天就這樣把我們鎖在警車裏,我不停地喊叫,車外的惡警衝著我直嚷嚷;「喊也沒用,等會兒電視台來了再喊。」我感覺有點不對勁,我努力使自己冷靜下來,我開始發正念,清除另外空間操縱電視台惡人的警察,不准他們來錄像。外面還有消防人員在來回走動,我當時沒想明白,消防隊怎麼也來了,而且還戴著頭盔,我沒有想太多,只是盡力控制自己冷靜下來發正念,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關押我們,必須馬上放我們走。後來聽到車外的一個惡人說:「抓這些人真過癮,去年冬天蹲過一回坑,抓到一個二千元,人抓到了馬上就給錢。」中共江氏流氓集團正是利用了人的這一點,不斷地用金錢誘惑收買陪葬者。
直到下午四、五點鐘的樣子,電視台也沒來,人也漸漸地散了,他們把我們分開帶走了,我被交給110送到了收容站,收容站拒收,去送的人和收容站的負責人都吵起來了。晚上六點鐘的樣子他們又氣呼呼地把我送到了第五醫院,在去醫院的路上我才知道他們一天的陰謀,押車的警察(好像是個小頭頭)氣呼呼地發著牢騷;「這弄的甚麼事,讓我們兄弟在外面搞了一天,東西都準備好了,電視台也沒來,把我們當甚麼了。」這時我才明白過來,他們又想製造假現場,矇蔽百姓,太卑鄙了。
他們把我送到五院就不管了,說先放一宿,明天再把我送到第七醫院(精神病院),我不會承認這一切迫害,又一次光著腳,慢慢地一步步地踉踉蹌蹌的走出了醫院,逃離了魔掌……
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在我腰椎骨折的情況下,三次被綁架,如果不是大法的神威,我可能早是個廢人了,而這其中的神奇與痛苦也是一個常人所無法想像和做到的。
第六次:在後來的日子裏,我便開始了流離失所的生活,我找不到同修,也沒地方住。我拖著幾乎不能走路的身體流浪在大街上,還得躲避警察的盤查,晚上我也便露宿街頭,在那個時候,如果沒有對大法的正信,真的會崩潰的,會瘋掉的,那種恐怖的感覺,我不知道怎麼能形容出來,現在想起來,都不寒而慄。
幾經周折,我又拖著身體投奔外地的同修了,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吉林再一次被綁架。我被作為重點帶到了省安全局,在安全局,又一次被酷刑折磨,他們體罰我,打我、用電棍電我。
十二月二十四日,我被非法押回當地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堅決抵制迫害,絕食抗議,被強行灌食,打罵、侮辱,獄醫還邊打邊罵:「就你這樣的,打死也白打……」後來我被送到馬三家,非法勞教兩年,體檢時,因身體狀況很差,說甚麼也不要,警察想給錢買通(在車上打電話時聽到的),也沒好使。結果當天晚上,我就從馬三家被帶回,由當地派出所帶家人把我接回家。
在二零零一年七月,我離家後不久,我的父親就去世了,當時因怕連累家人,一直不敢給家裏打電話,當我再一次回家時,我才知道我再也見不到父親了,我悲痛萬分,這場迫害,我們承受了多少無名的苦難?這場迫害,有多少個家庭在發生著悲劇,這場迫害,害死了多少無辜的生命?淚水,只有滿臉的淚水。
第七次:回家後,我無法平靜下來,我還在想著監獄裏那些每天都在發生的殘酷迫害,那些不知生死的同修,我每天都會想起那些迫害的場面,我的心裏每天都在恐懼中掙扎著,反思著,煎熬著,我知道迫害一天不結束,我就一天不能停止下來。
我在家休養了一段時間,臘月二十三,我跟家裏要了二百元錢,又拖著身體,艱難的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車,幾經周折,我到了天安門,喊出我壓在心裏很久的話:「法輪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輪功」,結果可想而知,一群武警蜂擁而上,對我拳打腳踢,又一次把我塞進了警車,我被押到站前派出所,晚上的時候和一些來自不同地方的大法弟子一起被送到了宣武門監獄,我的身體根本就經不起這般摧殘,到了宣武門,我已經不能走路了,檢查結果還是腰椎骨折,剛剛恢復一點的腰椎,再次斷裂,那時我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為了證實大法,我甚麼都不怕了,在那裏,我又開始絕食抗議,審訊時也沒報姓名,我擔心報了名又把我押回看守所了,臘月二十九的晚上,他們把我送到火車上,給了我一個拐杖,讓我自己找回家。
第八次:由於長期的迫害,我的身體一直沒能完全康復,沒有錢生活,又沒有身份證,生活起居都是問題,我過著流離失所的生活,身心無時無刻不在承受著巨大的痛苦。有一個同修做某產品的代理,二零零六年八月一號,他讓我去他那裏做推銷產品活動。沒想到在剛去的第二天,也就是二零零六年八月二日下午兩點左右,我們一行七人開麵包車出去推銷產品,在開發區灣裏附近的一個橋上,被灣裏派出所綁架(當時有一個五十幾歲的男人擋在麵包車前,手裏拿著一本《九評》就說是我們發的,後來據說是在單位被跟蹤到這裏來的,警察故意製造假相,據分析這是一場有預謀的綁架),惡警扣押了麵包車,無理綁架車上所有人。
我不配合他們的任何要求,他們就打我,警察還恐嚇我說:「有的是辦法收拾你」,我們被非法關押在開發區看守所。三號,我和另外幾個同修被非法送到姚家看守所關押。
在看守所裏,我再一次受到了非人的酷刑折磨,我的身體根本就無法承受這種非人的酷刑,剛進去沒幾天,我的腰椎就舊病復發,處於癱瘓狀態,左腿失去知覺,每次去審訊的時候,刑事犯就沒命似的拖著我出去,每次都疼的嗷嗷著叫,他們晚上不讓我睡覺,甚至不讓我躺著,白天坐監的時候還要腰挺直坐著,可是我的腰根本就無法承受的了。我開始絕食抗議。我絕食,他們就野蠻的灌我,每次灌食,我的身體就像散架了一樣的疼,有一次,他們把導管插到我的氣管裏,差一點被嗆死。他們把我打上背銬,戴上腳銬子,不斷地變著花招折磨我,他們白天黑夜不讓我躺著,到後來,我的身體幾乎成兩截了,我的頭幾乎要貼到腿上了。
有一次灌食完後,他們嫌麻煩,把導管留在裏面,不拔出來,我連呼吸都困難,晚上趁看管的犯人不注意,我把導管拔出來,結果被一頓毒打。他們唆使犯人打我,把我拖到地上,不讓我在板鋪上坐,當時正趕上我來月經,他們也不管,行動不了,上廁所都得爬著走,勞教的犯人嫌我擋道,就莫名其妙的打我一頓。那段時間,我真的不知是怎麼過來的,我只知道我還活著,我必須活著。
還有一次,他們把我拖到醫務室,強行給我灌了一些東西,回到監號裏,我就感到胃裏像著火了一樣,口很渴很渴的,我當時也不知道是甚麼東西,就不停地喝水,後來他們水也不給我喝,我感到其中必有陰謀,當時明慧網上有很多這樣的報導,他們就是在做人體試驗,我很明確,絕食的目的是為了抗議對我的迫害,並不是想死,如果我真的死了,他們就會造謠說我不吃飯餓死的。我藉著上廁所的時間喝沖廁所的水,因為我知道我不能死,一定不能死。
那幾天,他們白天晚上都監視著我,晚上我打了幾個盹他們都會彙報的,三、四天後,我緩過來了,事情過後,聽外面打雜的犯人透露說是灌了一袋食鹽還有別的甚麼東西。
還有一次,他們唆使犯人給我灌食,十來個人把我拖到廁所邊的窗台邊,把我的頭往後仰,按在窗台上,把我的頭,身體全壓住,不讓我動,要灌我,我也看不到他們要灌甚麼東西,怕謀害,就緊閉著嘴,咬緊牙齒,他們就野蠻的撬我的嘴,好像是很堅硬的東西,我當時被撬的滿嘴都是血,臉上脖子上都是,那個牢頭當時都噁心得吐了,我當時疼的直蹦,掙扎也沒用,當時監號裏一片混亂,後來一個男警察在監控裏喊話,他們才停下來,我的嘴當時都麻木了,不會說話了,牙齒鑽心的疼。
沒一會兒,他們又把我拖到地上,沒命的打我,有個賣淫的犯人叫胡晶,據說是吉林梅河口人,用指甲蓋掐我的敏感處,腋窩、上肘裏側,大腿根、臉,脖子,拔我的陰毛,發出鬼一般的笑聲,猙獰的臉孔,那時真的感到了甚麼叫獸性,太恐怖了。
我的全身被掐的青一塊,紫一塊的,鑽心的疼,牙齒好幾天都是木的,連喝水都疼,我的牙齒受到了最殘忍的迫害,後來牙齒就開始慢慢地鬆動,現在我的牙齒一個都保留不住,才四十多歲的人,已經是滿口假牙了。
身心的迫害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精神上的摧殘更是一種無形的迫害。現在想想都後怕,這些年來,那種恐怖的陰影一直都無法抹去。但我知道還有千千萬萬的大法弟子還在承受著無名的迫害,我必須揭露這種非人道的迫害。
即使這樣,警察也沒有放我,在絕食抗議三十多天的情況下,被警察非法勞教兩年,送馬三家教養院時體檢不合格,於九月五日晚回到家中。
第九次: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四日,在租房處被日新派出所惡警綁架。當時一起被綁架的還有兩個同修,早七點多,同修史紅波像以往一樣去上班,剛走到小區大門口就被三個不明身份的人綁架了。之後三個人非法闖進民宅,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在屋裏又綁架了我和另一個同修。我們當時就被野蠻的戴上手銬。問他們為甚麼抓人,是幹甚麼的,他們只是說:「跟蹤這麼長時間一點警覺沒有嗎?」並不說明他們的身份。
他們又叫來五個警察進行非法抄家。我因阻止他們的非法行為被毆打,還野蠻的強制我跪在地上照相。因不配合他們的非法要求,我再次遭到毆打。大約十點多,中共警察們把屋裏洗劫一空,其中台式電腦兩台、打印機四台、刻錄機一部、掃描儀一台、塑封機一台、移動硬盤四個、照相機一部、切紙刀兩把、錄音機兩台、復讀機一台、mp3工作用品,還有大法師父像片、大法書籍、講法光盤、講法磁帶、等大法資料。抽屜裏所有平時用的東西也都被倒空,就連針線、包、鉛筆頭、還有日常用的螺絲刀、剪刀、指甲刀等等生活物品都被洗劫一空。
他們翻箱倒櫃也沒有找到錢,其中一個人還說:「怎麼會沒有呢?」結果他們唯一找到的是我包裏準備交下個季度房租款的七百多塊錢。而同修的天霸表,當時被有個叫楊家茗的矮個子和一個瘦長臉戴眼鏡的人還在手裏擺弄過,後來,同修的母親去派出所要表時,警察們卻說:沒看見。這就是中共警察幹的下三濫的勾當。
中共邪黨人員們在往車上綁架時,把我倆的頭部都用塑料袋套上,說是怕被拍照。我當時只是穿件短袖和夏天的褲子,連外衣也沒讓穿,腳上是拖鞋。因喊:法輪大法好,再次被惡黨警察們打倒在地,連踢帶打拖進車,鞋也被拖掉了。邪黨人員把我按倒在車上,還用腳踢。被打著背銬,趴在車上已不能動彈。我當時就不會動彈了。
大約十一點多鐘我們被帶到大連西崗區日新派出所。年歲大的同修當晚被放回,警察只是從我包中搜走的七百多塊錢中拿出一百元給了老人就不管了。孤苦伶仃的老人一個人回到了被洗劫後亂七八糟的屋子裏,我與另一個同修於十月十五日晚被非法送往姚家看守所。
在連續迫害中,我因遭受酷刑折磨使身體多次被嚴重摧殘,沒能等到康復就又被綁架。十月十四日被中共警察們綁架毆打和拖拽後,我就無法行走,左腿不好使,腰也抬不起來。
在姚家看守所,我再次絕食抗議,再次被野蠻灌食,被折磨二十多天,已無法自理。期間到醫院檢查發現椎骨斷裂錯位,他們連拍的片子也不敢給我看,家屬要看片子也沒給。
在這種身心被嚴重摧殘的情況下,中共人員們不但不馬上放人,還毫無人性的對我進行非法勞教兩年,於十一月五日強行送往瀋陽馬三家教養院,教養院怕擔責任拒收,他們才不得不把我送回租房處。非法辦案警察寧永剛、劉山、趙某某將我扔在樓下道邊就不管了。後來,好心的居民把我背回屋裏。有看到這一幕的居民說:「這哪是人幹的事,簡直是一幫土匪」。
同修史紅波,被非法勞教一年半,二零零八年於十一月六日非法送往大連教養院關押,後來受到種種酷刑折磨,含冤離世。
中共警察就是這樣對待以「真、善、忍」為行事準則的好人的,天理難容!在此呼籲世界上的各種組織、正義人士能關注千千萬萬因信仰「真、善、忍」而被迫害的好人!制止中共摧殘好人的暴行,法辦元凶江澤民!
二零零六年八月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大連市灣裏派出所成員有
所長 王培重 0411-88964110
教導員劉基新 0411-88969752
警長於華俊 0411-88969759
惡警孫俊哲 0411-88969753
趙金鑫等 0411-88969757
灣裏派出所所長叫王培重,據說,王培重是從別處剛調到這裏來的。
大連開發區看守所:87655257、87635074、87635288
大連開發區看守所主要負責人:
孫忠海的住宅電話:87303488
隋學文的住宅電話:87583636
大隊長:邢汝家、政委:傅文清、副大隊長:孫忠海
大連姚家看守所
地 址:大連市甘井子區姚家街270號
總值班室:0411-83792702
姚家女監區(8區):0411-83792763
總 機:0411-83631881
大連市甘井子區姚家街270 號郵編:116031
大連市姚家看守所電話(區號 0411):
0411--86886166、86887811、86887816、86887815、86887813、86887812、86870718、86870728、86870857、86870508、86871988、83792725
傳真:0411--86871844
總機:0411--86871181
值班室:0411--83792702
監獄長:0411--86871422
政委室:0411--86870181
管教監獄長室:0411--86872399
(註﹕以下電話均為2007年度的,有可能已變更)林強:邪黨西崗區委副書記,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分管西崗區政法系統。1956年9月出生,漢族,山東煙台人。邪黨省委黨校研究生。
辦公電話:83636590 宅電:83789751 手機:13387860088
王玢:邪黨西崗區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漢族,1955年2月出生,大學學歷,曾任西崗區組織部長,政法委書記。
辦公電話:83635350 宅電:83789255 手機:13304095679
杜滿卿:邪黨西崗區政法委專職副書記。建立西崗區反邪教網。2006年4月19日,在全市政法工作會議上,西崗區610辦公室獲得由市反×教領導小組辦公室頒發的2005年度市「爭先創優」活動優秀成果獎。
大連市西崗區公安分局公民監督投訴電話:
國保大隊王大隊長,劉賢軍副大隊長
0411─ 83796107
82474732
82474777(夜間)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東北路146號西崗分局
日新街派出所位於兒童醫院附近,有關人員電話:
總機0411-83793730
武樂明,所長,電話13304112228
孫忠忱,副所長,電話13130414212
郭亮,副所長,電話13500712025
鄒長江,教導員,電話0411-82957058
陶義臣,13889699009
楊家名,13930039577
寧永剛,13198466608(參與綁架,抄家搶劫)
劉山,13998612037(也可能13998312037)(參與綁架,抄家搶劫)
趙某某(參與綁架,抄家搶劫)
孫邦棟,15998503777
孫曉東,0411-82987398
大連市西崗區政法委
大連市西崗區北京街西崗區政府,話:0411-83635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