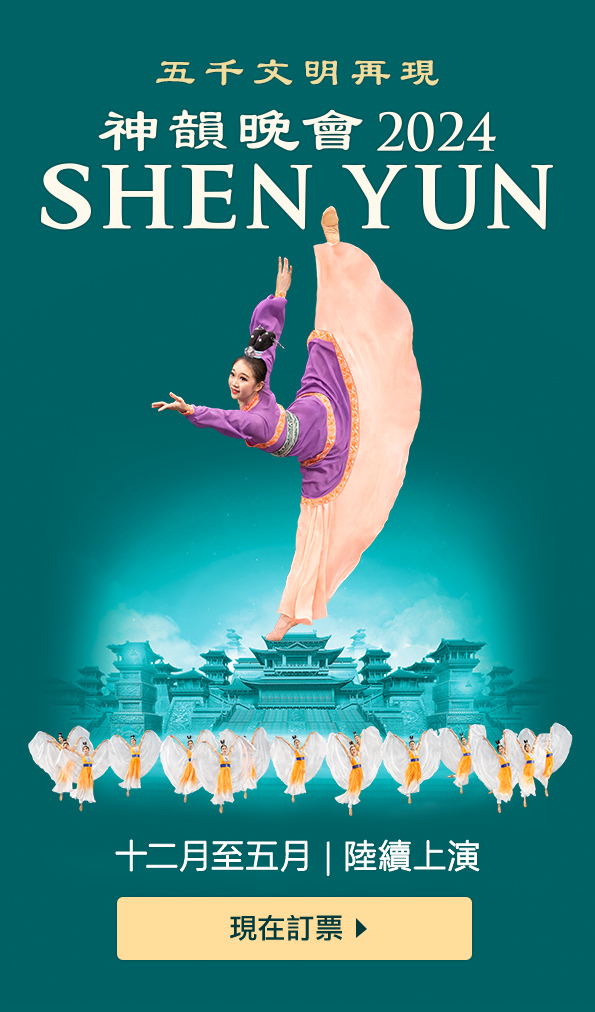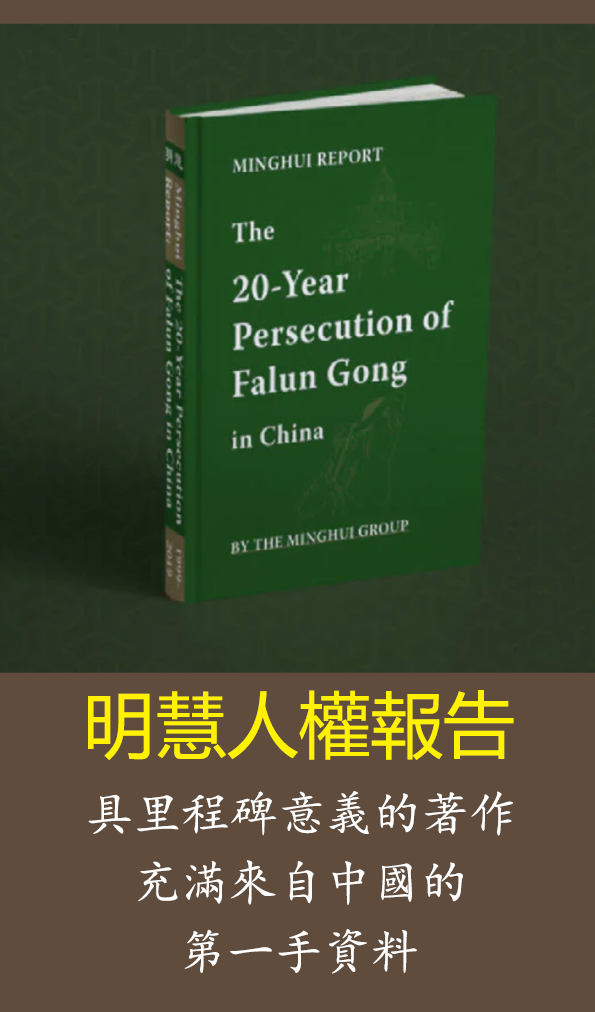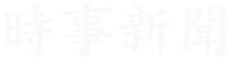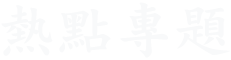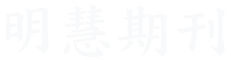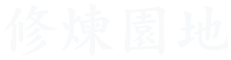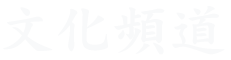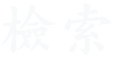以色列馬裏夫週末雜誌:從中國監獄裏歸來(下)
媒體問題
媒體確實在整個過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法輪功學員們相信世界媒體將會正面報導,記錄整個事件,使事件大面積曝光,他們被捕的照片將阻止中國當局監禁他們。
「他們事先準備了媒體聲明,只要一知道他們被捕的消息,就將聲明放到他們的因特網上去。里斯海還準備了一份個人聲明。他們準備了一個細緻的行動計劃,以備他們被捕時用。除此之外,也邀請了媒體記錄這一事件。」
「我還竭力提出了其他理由來論爭,比如,我說,如果他繼續在加利福尼亞積極參與法輪功的活動,而不是在中國的監獄裏浪費時間,這對法輪功運動和人類都會更好。結果還是說服不了他。」
「我們擺出的所有理由都沒有說服他。我逐漸認識到我們不僅勸阻不了他,而且從道德的立場來說,我的這種做法也站不住腳,尤其是當他說出這話以後--他說:『媽媽,您設想一下,假如奈爾遜.曼德拉和聖雄甘地因為他們母親的擔心而讓步的話,那世界會是甚麼樣子?』我不得不承認我無言以答。」
「作為一個母親,她當然不想讓她的兒子處於危險之中,但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我能跟他說甚麼呢?確實,沒有那些甘冒風險的人的勇敢行動,就不會發生任何改變。他還跟我說:『從小到大,你就是這樣教育我的。』他說的是對的。他在一個活動家家庭中長大,對社會上發生的事件耳聞目睹。從小他就隨我們一起在以色列和美國參加抗議活動。所以,我不可能跟他說:這些行動是一回事,而當真正的危險局面出現時,就順從你父母之意吧,他們在為你的生命擔憂呢。他的父親彼得是在美國長大的,他拒絕去越南打仗,在美國積極參與人權運動。他一直在以色列積極尋求和平共存。1973年他已經在呼籲實行兩個國家(以色列國和巴勒斯坦國)共存的解決方案。里斯海就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裏長大的,並吸收了我們的價值觀。」
「當我意識到我勸阻不了他,我就開始琢磨怎麼來幫助他減少危險,怎麼幫助他做好準備。」
大學裏的行動中心
「根據最可能發生的情況來看,我們認為他會被捕,也許會失蹤。所以我們決定一知道他被捕的消息,就馬上通知媒體。這樣就會讓中國當局很難將他隱藏起來。所以我列出了打電話的名單--大使館、外交部的緊急號碼、媒體、認識某某人的人……」
「當我一聽到事情真的發生了時,我馬上就按照計劃去做了。我沒有驚慌,也沒有給自己留時間去想會發生甚麼情況。我覺得,當我們在與他的最後一次談話中告訴他,我們是多麼為他驕傲,我們是多麼支持他時,就好像也是在讓我們自己堅強起來。自從我們接受了他要去的這個事實開始,我就知道我必須對他有絕對的信心。」
星期二一早,在預定行動開始前的半個小時,拉米什博士趕到了她的辦公室,在門上掛上了「不要打擾」的牌子。在她兒子在中國開始打坐前的十分鐘,她想用她兒子的方式來支持他。「我跟我自己說,你現在要靜靜地坐下,集中思想發正念。我必須承認我試了,但我沒有靜下來。我打電話給正在英國出差的彼得。我們互相鼓勵,希望事情有個好的結果。接下來我就試著工作」。
「一個半小時以後,我收到他女朋友從美國打來的電話。里斯海從監獄裏打電話給她,讓我們知道他被捕了,情況還好。我立即給彼得打電話,接著我們就開始行動了。我告訴我自己,好,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我開始按原定計劃去做。雖然我是被捲進來的,但是既然我參與了,我就必須盡一切可能讓他獲得釋放,因為你就算坐在那兒哭,也於事無補。」
「我首先打電話給外交部緊急辦公室。他們告訴我如果里斯海是用美國護照進入中國的,那麼美國就要對他負責,這也許對他有好處,因為去那裏的美國人有好幾個,一群人比較容易獲得釋放。我感到時間非常難熬。我們知道他被捕了,而在短期內又沒有人能見到他。我不知道這種情況會持續多久,他是否安全?在甚麼情況下被關押的?我做好他也許會被關很久的準備。」
她在她大學辦公室設置的行動中心的電話響個不停,先是外交部,美國大使館的,然後是從報社,電台,網站,在英國的彼得,還有她兒子在美國的女朋友莎拉打來的。
「一度有傳言說,中國廣播電台報導說他們被捕了,要被驅逐出境。最讓我們擔憂的是法輪功的網站報導說有36名學員被捕,而中國的報導說只有35人。我們擔心那個失蹤的人。實際上在不同的網站上有各種各樣的數字和報導。沒有人知道真正發生了甚麼,每個人都是在引述別人說的。就這樣持續了24小時。我們設想了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但我們知道既然他已決心不簽任何聲明,他可能會被關進監獄。」
被捕
與此同時,里斯海已經在中國被逮捕。他和他的朋友布雷德於四天前抵達中國。他們倆住進了北京的一家旅館,他們很快就發現了有隱蔽攝像機,這顯然是那兒的所有旅館房間的設施之一。
為了不引起懷疑,他們在一間很暗的房間的角落裏煉法輪功,這樣攝影機就看不到他們。第二天一早,他們去了紫禁城和天安門廣場去查看場地。里斯海說「我記得,我當時想這不是真的。我好像是在夢裏一樣。這兒就是發生了許多歷史事件的遼闊廣場,我作為一名法輪功學員來到這裏,卻沒人知道。我對自己說,兩天後我還會來這兒,沒有人知道將會發生甚麼。那兒出奇的靜,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但在表面的正常底下,確實隱藏著不正常。」
20號的早上,他們倆做好了儘快離開中國的準備。他們將所帶物品寄存在了機場,以便準備好當天下午乘預定飛機返航。到廣場的路上,里斯海用不大靈光的中文跟出租司機交談,他了解到司機對中國(江澤民)政府不滿。但他儘量克制著自己,未告訴司機他們同意他的觀點和他們現在是在去抗議這個(江澤民)政府。早上10點鐘,他們購買了進紫禁城的票,以防萬一他們想很快跑掉時可以混在數百的遊客人群中。他們還購買了地鐵票,找好了所有可以走脫的路線。
「午餐時,各種的恐懼感向我襲來,但我勇敢地正視這些恐懼,讓我自己平靜下來,讓內心平靜下來。我提醒自己我們為甚麼要來這兒--是為了來幫助別人。這使我得以將注意力集中到他們的處境上,而忘掉了我自己。吃過午飯,我們向廣場走去,找了個椅子坐了下來,等待著。時間過得很慢,我的心不時難以控制地撲撲跳著。1點50分,我們向指定地點走去。從遠處,我們看到了一些同修,於是知道我們不會孤單。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員們,甚至大部份素不相識,然而為了完成一個共同的使命而結成了一體,實在是鼓舞人心。我們見面了,互相握手。然後我們就這樣坐在了地上。我們看到周圍圍上來許多人,他們都在好奇地看著。」
「我們看到一些警察懷疑我們在幹甚麼。我看到警車正向我們靠近。我們說聲『開始』,就開始脫鞋。在我們的後面,橫幅展開了。我們單手立掌於胸前,這種源自中國的古老姿勢,現在用來捍衛人權。」
「我合上了雙眼。我聽到警笛聲,輪胎的刺耳聲,車門的開關聲,警察疾奔而來的腳步聲。我仍然雙眼微閉,因為我認為我沒有做任何不對的事。我跟自己說,我在這兒能堅持多久就堅持多久。我聽到我周圍到處是奔跑聲,我發現自己心生笑意。我心想,我在這裏了!我正同來自世界各國的35位學員在天安門廣場打坐,向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傳達我們的訊息。我們都集中意念,保持平靜,互相支持。雖然我在的地方是其他人曾被謀殺的地方,我卻很平靜。」
「這時,噪雜聲一片,幾個人抓住了我。我沒有反抗,而是集中意念將我的重量壓向地面。他們拉開我的右手,但我輕而易舉地將手抽了回來,又恢復了單手立掌。我對自己說,我要在這兒堅持下去,我越來越重,他們抬不動我。我確實感到自己很重,但突然我產生了恐懼感,就在這一刻,他們抬起了我,使我站立起來。他們將我拖向警車。他們拖我的時候,我一遍一遍地喊著「法輪大法好」,直到他們把我投入警車。」
被毆打以及回國
在警察局,學員們用他們的手提電話將他們被捕的消息告訴了世界。剛開始被盤問時,學員們解釋到他們是出於好意,但是,當他們拒絕在中文的文件上簽字時就受到毆打。一個警察抓住里斯海,打他,並用中文衝他喊叫。
「我告訴他我只會一點兒中文,我聽不懂他說的話。他惱羞成怒,站在我的面前用英文又嚷又罵:『你來這兒製造麻煩,(你要)尊敬我』。他狠狠打我的臉。我跟他說『你為甚麼打我?』我重複著我會說的其他中文。他氣瘋了,用力把我推向牆壁,用膝蓋在我的兩腿間撞。他開始問我問題,但我拒絕向他提供其他學員的情況,也不說任何對法輪功不好的話。」
學員們認為,由於他們的國際背景,中國當局不會將他們留在中國,事實果真如此。經過28小時的關押,他們被驅離出境。第二天夜裏11點45分,里斯海抵達了溫哥華,他又累又餓,赤著雙腳,因為他在被捕時鞋留在了廣場上。他打電話給他的母親,聲音洪亮而充滿了喜悅。他說:「我沒事兒,都結束了。」
不想做哭泣的母親
里斯海和他的母親從這件事中各自得出了結論。一位媒體研究人員(這位母親)自己成了一個重大事件發展過程中的中心人物,這種事並不會經常發生,而她,在此事件中不情願地成為了一位無辜被抓、被打的英雄的母親。這一事件肯定會給她提供許多專業素材,例如:以色列媒體婦女形像的研討會。
「我從這件事中學到了很多,關於我兒子,關於法輪大法,更主要的是關於媒體方面。多年來,我一直在研究媒體是怎麼描述婦女的,而這次,我驚訝於媒體是如何找我採訪的。按照媒體塑造『失去親人的女人』的模式,他們期待的是一位充滿感情,流著眼淚的母親,他們期待她這麼說:『我好害怕,如果抓人者可以聽到的話,請你不要傷害他。』他們期待的只是『我是誰誰的母親』而已。但是他們發現他們找到的這位女士講出的話卻很理智,她不願在電話上情緒失控。」
「耶蒂歐特.艾羅諾特(Yediot Ahronot)刊載了一整頁的文章。他們採訪了我很長的時間。然而他們引用我說的話只是『我們非常為他擔憂,為他擔驚受怕。我呼籲任何能幫助我們的人都伸出援手。』事實上我從未說過這樣的話,也沒有在任何時候向世界發出催人淚下的懇求。一個女人說出的明智、有理性的話是無足輕重的。」
「我講授這個題目,我也將從這個事件中大有收穫。很顯然,我們在媒體眼中的『角色』就是甚麼人的母親,甚麼人的寡婦,甚麼人的太太,總是哭泣著,總是可憐的受害者,沒有能力說出任何明智的話。」
「我們在媒體中的地位不是作為女人的角色,就是母親的角色。在以色列的媒體中,這意味著男人的最大犧牲就是作為戰士為國捐軀。而女人的最大犧牲就是生孩子,並將他們撫養成人,讓他們成為軍人,為國捐軀。他們也把我看成是這樣的角色,這讓我覺得吃驚和荒謬。所以,在這些事件中,我發現我自己是在觀察媒體。我看著他們將我塑造成甚麼形像。而我拒絕完成他們想要我扮演的這種片面的角色。那不是我。我跟記者談了很久,給了他們很多資料,而編輯們認為人們應該聽到的只是這名女士很擔憂,想讓他獲得釋放。」
「除此之外,我還發現自己不自覺地成了法輪功的發言人。我開始閱讀有關法輪功的資料以便講起來更有智慧,我開始越來越多地理解了(法輪功)。我不能說我煉這個功法,但我認為所有這一切都對我產生了影響。我確實認為我是有理性的人,我在有理性的地方--大學上班。然而,我們也知道科學並不能解答我們所有的問題。」
「當我聽到他們在監獄中的經歷,以及他們是怎樣影響看管他們的警衛,他們是怎樣承受肉體的傷害而不覺得疼痛,這讓我不禁自問,我們到底是否真的了解我們生命的精神一面?我們是否真的懂得這些?這些問題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有很長時間,我都擔心我們會面臨無法跟里斯海溝通,擔心我們可能會失去他,但同時,我看到的都是正面的事情。法輪功沒有領袖,與錢無關,沒有宗教規矩,沒有宗教儀式。我想挑出毛病,但怎麼也找不到。」
在里斯海看來,他相信他們達到了目的。幾百萬的人聽到了他們的訊息,那就是:面對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的迫害,世界不應該沉默。
「有甚麼理由去毆打一位在公共場所坐在『真、善、忍』橫幅下的人呢?幾週前有多少人知道法輪功,知道他只不過是一種修煉方法?現在許多人都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由於我們的努力,使更多的人清醒了。我相信這將導致更多的人站出來,為事實作證,支持講清真相的努力,反對人權侵犯行為。這就是我們努力做到的,我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傳遞這些訊息。」
……至於為甚麼一個以色列公民要為了中國的人權而去冒生命危險,他好像已經準備好了答案:『許多人問我,你為甚麼不為巴勒斯坦人的權利而鬥爭?你為甚麼不反對以色列的社會不平等?你為甚麼不反對破壞熱帶雨林,等等。在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錯的。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些事情上。但我認為中國發生的事很特別,因為有兩個非常明顯的對抗力量--一邊是追求和平、寧靜和善良的一個群體,而另一邊是跟他們完全相反的。我決定行動是因為我在其他的衝突中找不到如此大的對立。我修煉法輪功,因為他給我的生命帶來了巨大改變。我非常榮幸能有機會為法輪功說話。我想獻出我的一份力量,因為我不能想像在當今的世界會有人只是因為想作好人就被謀殺。」
(彼得.拉米什翻譯)
2001年12月1日
譯註﹕在天安門廣場被捕的以色列學員的父母,均是不修煉的人,他們在整個事件中提供了大量的幫助。他的父親特將此文從希伯來文翻譯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