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郴州雷保良在勞教所、看守所遭受的摧殘
二零二一年五月八日上午,郴州燕泉路派出所陳所長帶著兩個警察闖入雷保良老人的住處騷擾,將近四個小時之後才離開。他們呆這麼久,像是在等其他法輪功學員去雷保良家。
下面是雷保良老人訴述她的經歷:
我叫雷保良,女,今年77歲,湖南省郴州市人。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是偶然遇到一位大爺,從而接觸到法輪大法的。這位大爺滿面笑容,慈祥善良的樣子讓我感到很親切。我問大爺:「大伯,你胸前佩戴的東西是甚麼啊?」他說:「這是法輪功的徽章。」原來他是煉法輪功的。我就一問到底,並且跟著他到了他家。大爺看我有心想要學煉法輪功,就送給了我一本書《法輪功》。
得法獲新生
當我第一次接到金燦燦的大法寶書時,如獲珍寶。翻開第一頁,我看到了師父的照片,師父很慈悲。我頓時覺的自己多年飄零的身心像是突然找到了根,我終於找到了自己回家的路,找到了領自己回家的師父了!
修煉法輪大法之前,我百病纏身:腰椎間盤突出、血小板減少、腳關節腫大、乙型肝炎、類風濕、皮膚長瘋團、左腦後遺症、鼻息肉、先天性弱視、滿臉布滿黑斑、肺氣腫咳嗽起來像放鞭炮,越到後來呼吸困難,氣管被棉球堵塞似的、耳鳴、有時還突然講話沒有聲音、便秘、乳房腫瘤接近晚期、低燒,長期陣冷陣寒。
就這樣一個百病纏身、幾乎像一個廢人一般的我,在修煉法輪大法之後,所有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飛了。那種完全沒有病的狀態,是我從小到大從來都沒有體驗過的,我就像換了一個人一樣。
修煉法輪功讓我明白了人活著的真正意義。師父把宇宙的真理傳授給了我,讓我得到了這萬古難遇的修煉的機緣。我的精神得到了充實,道德品質得到了提升。從此,我的人生有了目標,知道了如何做人,如何處事,不再渾渾噩噩、迷迷瞪瞪的活著了。
法輪大法直指人心,明確了修煉心性是長功的關鍵,心性多高,功多高,強調重德行善做好人。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問題,師父都像開鎖一樣打開了我的心結。師父用最淺白的語言給我們弟子講述了高深的法理。自從我修煉法輪功以後,我內心世界的變化簡直太大了,心胸變的開闊了,氣量也變大了。能理解別人,容忍別人,善待別人。我的心性在突飛猛進的直線昇華,是師父在直接把我們往正道上引領。
一九九四年元月六日,我參加了師父在廣州辦的法輪功面授班。在廣州學習班期間,我在公交車上,一個乘客把車窗用力使勁一推,把我的手割破出了血。我很快把手含在嘴裏,怕對方看到引起他難過。如果我不修煉法輪功,我不會有這樣的善心。
有一次,我在鄭州撿到了一個錢包,當時我自己的行李都顧不得拿,馬上直接找到了失主。當時失主都覺的簡直太不可思議了。這都是我原來做不到的。學了法輪大法,真是心境遼闊,再大的仇恨都可以拋到九霄雲外。
我在農村建房的磚瓦、木材、地皮都被前夫的兄弟佔有了。我當時想等小孩大了以後再去算這筆賬。可是修煉法輪功後,我有了不同的想法。我一直沒有告訴兒女,怕他們會找人家的麻煩。再說修煉人也不能挑起仇恨,所以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以前我父親被徵兵入伍,我二伯母嫉妒我父親繼承了新房產,狠心詛咒我父親死在外面。後來不久,我父親真的死在了路上。我三歲時,我母親就改嫁了。從此,我成了孤兒。為此,我對二伯母怨恨的心從未放下過。修煉法輪大法之後,我明白了人各有命。讓別人佔點利益,也不用記在心上;否則,恩恩怨怨何時才能了結?所以再大的怨恨也就一筆勾銷了。
還有一次,一輛麵包車違規行駛,把我撞倒在地上,我當時說話氣都接不上來了。我大聲說:「我是煉法輪大法的,不會有問題,你們先走吧。」我用手使勁招呼要他們都走,然後自己用力爬起來就走上了大馬路。我回頭望望他們,他們竟然還原地站著,動都不動,可能他們真的是被今天的奇蹟給驚呆了吧。雖然被車撞了,但我仍然盡了法輪功學員的善心,按照大法師父的法去修自己。
講真相 遭殘酷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澤民邪惡集團開始迫害法輪大法。十月二十五日,我去北京上訪,為法輪功討公道,講真相。可是,很多法輪功學員被北京火車站派出所綁架,我也如此。第二天,他們非法把我轉押到郴州駐京辦事處。我在那裏被非法關了三個晚上,我單位和當地公安過來接我。郴州駐京辦事處的人要單位交了二千七百元錢後,我才被放出來。後來,這筆錢從我的工資裏面非法扣除。
我一回到郴州,剛下火車,一群公安人員拿著攝像設備給我們非法攝像。然後把我送到單位賓館非法關押,並且單位輪流派值班人員對我進行非法監視。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左右,單位廖書記等人送我回到家,並且要我交出大法書籍,我沒有交。同一天,公安局一個姓何的警察也逼我交書,並逼我兒子開著單位的小車把我劫持到桂門嶺拘留所非法關押。在桂門嶺拘留所,我被迫害了十五天後,又被轉送到了郴州第一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被非法關押了三個多月後,於二零零零年三月,我被非法勞教兩年,被劫持到湖南株洲白馬壟勞教所。勞教所找藉口說我不「轉化」,不服獄警,加期半年。我實際被非法勞教了兩年半。
當我一進株洲白馬壟勞教所,就被強行搜身。把我所帶的衣服都倒地上,一寸一寸的摸。把我的新皮鞋從裏面割爛,目的是搜大法經文。勞教所迫害法輪功的大隊長丁彩蘭為了達到「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指標,對法輪功學員用盡各種殘酷手段迫害。成立嚴管隊、攻堅隊,用欺騙、威逼、利誘等各種惡劣、高壓的手段「轉化」法輪功學員。
1、酷刑「打禾」、「剝老虎皮」
當時勞教所為了逼迫我「轉化」,採取了極其惡毒的手段,幾十個人集中迫害一個人。幾個身材高大的人把我抬起來,再用力摔在地上,著地的那一瞬間,腦袋就像開花一樣,眼冒金星。如此反覆的長時間連續下來,導致我下身流血,內臟傷痛,肋骨處高高凸起。她們把這個迫害人的方式叫「打禾」。
為了達到讓我更加痛不欲生的目的,想把我的肝區直接拍壞,所以對我的兩肋使勁拍打。一群人用手在我身上抓、掐。掐肩的頂部,直接麻痺左右大腦這條大骨筋;拽、揪、拍、砍。從頭上開始,用手指頭使勁往裏摳頭部,整個頭都麻木了,她們叫「扒蛇皮」、「剝老虎皮」;用手砍脖子、砍後腦勺、砍頭頂;一個勁的搧耳光。有一個邪悟的人是衡陽的,打的手痛了還不停手,還在奮力打我的臉。打累了,就讓我去面壁,說明天接著再打。
2、扯眼皮、拽耳朵、砍脖頸子
在那裏,每天第一件事就是進電視房,聽馬三家演講洗腦。我不聽、不看,在心裏背著大法師父的《論語》。她們就過來扯我的眼皮,把我眼皮翻上來、翻下去;還拽耳朵;還逼我寫認識。跟我說:「來這是幹甚麼的!就是轉化你的!聽了那麼多還不轉變,變不變!」我說:「要出淤泥而不染。」她們一下子跳起來,喊:「再打!再不悟再打!不轉也得轉!」她們立掌猛砍我的腦後脖子,而且是兩個手掌同時使勁。還對著耳朵打,頓時我的耳朵甚麼都聽不到了,只聽到轟轟的響。
有時她們拿紙捲個筒,對著耳朵大聲吼叫,她們叫「轟炸」;用手砍後腦勺,砍的又紅又腫,她們叫「砍狐狸頭」;使勁掐穴位,長時間掐腋窩、鎖骨、耳朵等等多處敏感部位,被她們掐過的地方傷痕累累;用手指掐頭皮,連頭髮一起往起拔;把頭髮都撥拉到臉上,達到醜化我、侮辱我的目的。幾個小時折磨下來,我的衣服紐扣都被扯掉了,衣服被她們的手抓得都發臭了,身上沒有一塊好肉,都是紫的。
 酷刑演示:暴打 |
不打我的時候,她們就在我耳邊罵大法、罵大法師父,罵我,對我的人格進行侮辱。我被這樣活活的折磨了十八天之久,身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真正是痛不欲生!有人說馬三家黑窩裏學來的整人的邪惡手段都用盡了。這時候,勞教所領導趙貴保和一個女所長來了,我要趙貴保看我被打的又紅又腫的地方。趙貴保說這是誰把你打成這個樣子。我說沒有人安排,她們也不敢這麼做,何況這麼久了是會要出人命的,我一定會曝光這次殘暴。在這個黑窩裏,就算是打死人也是被白打死,也會說和這裏無關。
3、時時監控毒打
在勞教所,二十四小時都是被監視著的,就算是入睡都有人盯著你。最可笑的是,當時我的床上被擋了一塊布,不讓別人看到裏面是誰,門上也掛著一塊布擋著,不讓人看。可能她們做盡傷天害理的事情也心虛吧,而且大概也是要把我往死裏整做的準備吧。
夜晚我無法入睡,想通過煉功打坐康復一下傷痕累累的身體。不到一分鐘,我的腿就被猶大給拖下來了。深夜又對我進行了一輪圍攻迫害。到第二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有個良心尚存的人摸著我的肋骨,我告訴她這裏痛。我聽她在說不要繼續打了,再打就會出人命了。
4、關在半山腰的小號裏折磨
二零零一年元月,因為我堅持信仰真、善、忍,他們把我非法關在半山腰的小號裏二十八天。小號裏面只有塊水泥板當床用,一張破棉絮只能放地上冰著。一個坑當便池,裏面堆滿了大便。有一個水龍頭,但是沒有水。還有一個專門迫害人的門,讓人在上面撐不直,也蹲不下。
特警副隊長潘向東用手銬扣住我的雙手,再用一根長長的鐵鏈拴住,猛的往下一拽,我身體往前一栽,幾乎要倒在地上,手銬深深的卡進了我的手腕,像刀割一樣劇痛。然後,把我拖到垃圾旁邊的桔子樹下,雙手反銬在樹上,整個頭用布包起來,只留鼻孔出氣,然後再用膠紙包紮實,讓我掙脫不了。
 中共酷刑示意圖:吊銬、固定銬、反銬在大樹上 |
進小號的時候又要銬我,我掙扎著不配合,一群人當時使勁把我推進了小號。特警正隊長譚湘謙要我跪下,我不從。他就從我身後猛踹一腳,我倒在地下,他把我抓起來,反銬在那扇特製的門上,我站不直、也蹲不下。晚上睡在一個剛好容一個人的水泥板上面,只有一床又髒又破的棉絮。白天,破絮放在地上冰起。在小號裏我被非法關了二十八天。頭兩天沒有給我送飯,餓到第三天才送飯進來。
5、關大禁閉室吊銬
從小禁閉室出來,又被一種殘酷的方式逼迫「轉化」。他們把十七個堅定的法輪功學員關到一起,叫大禁閉室。門口擺著一箱電棍,一箱手銬。不准我們上廁所,屋裏放著一個小桶,供十七個人大小便用。吃的東西都是從門縫裏塞進來,或者從地上門坎過去。那門是鐵圓柱的,不是鐵板,方便監控我們。除了幾個特警輪番監視外,只要認為有機可乘,一群吸毒人員隨時闖進來拖抓我們。只准我們吃喝,卻不准上廁所,其實就是變相的逼迫我們絕食。
二零零一年三月八日這天,我們不約而同的絕食反迫害。勞教所乘機用最惡毒的手段把我們往死裏整。他們把我們每個人的兩隻手往兩邊拉到極限,再銬到床的上鋪,一個接一個連銬起來,人沒有絲毫的活動餘地。只要其中有一個人動一下,連銬的所有人都要產生一陣劇痛。因為地面不夠寬,還有人像被串繩一樣,一串串的好幾個人吊銬在同一上鋪的柱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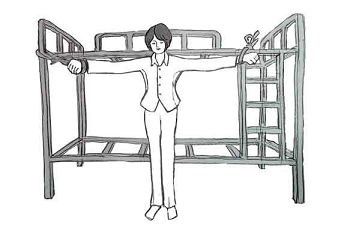 中共體罰示意圖:銬在床柱上 |
剛剛銬上時,給我們的腳下墊上一個東西,等全部銬完了,腳下的東西都被抽走,使我們腳沾不著地。頓時,手銬就陷進了肉裏,手腕鑽心的劇痛,頭發昏,人呼吸困難,就像心臟錯位了一樣。有的人休克了過去,有的人臉色慘白,豆大的汗珠往外冒。
6、野蠻灌輸摧殘、藥物迫害
更邪惡的手段是後面的灌食,由於手段過於殘忍,有人說看到眼睛翻白了不鬆手,導致第一個被拖進去灌食的左淑純就這麼活生生的被迫害致死了。之後,左淑純是被用門板抬出去的。因為要路過這個門口,所以大家都看見了。左淑純從頭到腳被蓋著,右手耷拉在外面。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八日,門口開來了一輛車,進來幾個特警。他們用暴力把我連拖帶抬的拽上車,鞋子掉地上了都不讓我穿回去。其中有一個叫唐隊長的女性,還有一個年輕的女性。他們把我劫持到了勞教所外的一家醫院,我看到有病人在那抽血。
我一來,一瞬間戒備森嚴,整個醫院看不見其他真正的病人了。醫生對我進行了各種檢測,強行從指尖取血化驗肝功能。接著,就將我推進一間房子,把我按在手術台上,進行內臟檢查,做CT檢查,還吊了幾瓶不明藥物。
我當時的身體狀況並沒有甚麼不適,我不明白他們為甚麼要用暴力的強制行為把我單獨拖到醫院裏來,對我的五臟六腑進行全面檢查。打吊針的時候,我不停的講法輪功真相,但沒有一個人吭聲。過程中,除了幾個醫生,還有一個我從未見過的男幹部守著。
從醫院回來後,又安排我住在勞教所醫務室,天天強迫我打吊針,和我一起打吊針的還有兩個法輪功學員。打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幾個法輪功學員發現身體都出現了很大的問題,膝蓋發軟,沒有了力氣,走路兩腳不聽使喚,與大腦協調不起來。其中一個法輪功學員夏晴更是嚴重到眼睛發直,流著口水,像是患了痴呆一樣,只能扶著牆壁走路。
7、「嚴管隊」虐待
我問他們:「你們這是打的甚麼東西?打出問題來了。我現在腳走路都走不穩了,我將來要曝光你們。」結果,就把我搞到「嚴管隊」去了。在那裏,天天坐小板凳,背朝外面,臉朝牆壁。坐小板凳也是酷刑,要求怎麼坐怎麼坐的姿勢都是邪惡研究出來的。人一身的重量都靠臀部尖那根骨尖在承受著。瘦的人坐一下就不行了。
有一天晚上,我睜開眼睛,看到一個腦袋伸到我面前,我嚇的喊了一聲。那人說:「我聽你是不是在背經文。」還有一天晚上,在沒有妨礙任何人的情況下我盤了一下腿,兩個警察就把我拖了出去,一直拖到辦公室。一個拖,一個用電棍猛擊我的左腳,打的我左腳連腳趾尖都是黑的。然後把我甩在辦公室地上。
有一次,一個高高胖胖的女陳隊長,拿了一隻杯子(我看到那杯子裏有白色粉),然後再裝上水,強行把我按在椅子上,再坐在我身上,還把我的手反過去,另外一個人又按住我的頭,撬開我的嘴,把那杯裝了不明粉末的水灌我。為了剝奪我的休息時間,經常到了晚上三點了也不讓我下班,藉口是趕任務加班。
8、被迫害的全身癱瘓
大約是二零零二年一月,當時我被迫害的全身癱瘓,上床都需要人把另一隻腳抬上去,手端不起碗,腳不能走路,吃飯都是人家餵。我的膝蓋腫的很大,膿血交加,而且全身發癢,長滿了比芝麻大一點的小疙瘩。癢的要命,一抓小疙瘩就冒血,結果一身皮膚全都潰爛了。身體直不起,因爛皮扯的裂縫痛,皮膚變成了多種顏色。剛開始皮膚是紅色的,爛過之後變成黑的、青的、黃的。因為我不放棄大法修煉,被非法多加半年。兩年半的非人生活,就如同掉進了妖魔洞裏,生不如死。
 中共酷刑示意圖:注射藥物 |
大約二零零一年五月初,由於他們往我身上打的毒針傷害了我的身體,使我吃不下飯。到了第五天,那個特警隊潘隊長把我拖到樓下一間陰森森的地下室裏。在那裏關了一個曹姓的老年法輪功學員,有個播放機一直播放邪悟的東西給他聽。這間房子地上墊的東西都有著人掙扎的痕跡,好像是灌食專用的。除遭酷刑之外,別人不會被關到這裏來。我被拽下來了,高個子抓住了我的頭髮使勁往牆壁上撞。
為了幫助那個法輪功學員的正念,我就背《論語》,念「法輪大法好!」那個播放機瞬間就停止播放了。潘隊長立即把我再往裏頭房間拖,離開了那個老年法輪功學員。再把我往鐵床下拖,把手銬固定在床鋪下,再擺放兩台機子放邪惡的東西想往我大腦裏灌,可是又沒有播放出來。不是沒電,就是機器出故障。他們還拿電棍電我的嘴,直到他們都離開地下室。我在床底下趴了不知道多久,才放了我。
本來我就是個疾病纏身的活死人,修煉法輪功才有了身體的健康。真、善、忍宇宙大法,這是我生命需要的,他們要我放棄修煉,那是要我的命!我怎能好壞不分善惡不明,人各有志,信仰自由。我吃不下飯,他們又再乘機對我灌食。這一次灌食捏著我的鼻子不放,然後用削尖的竹筒灌,劃破了我的喉嚨,我尖叫一聲,一陣劇痛。
有一次,我突然被喊去一個會議室,那裏有講台。我一進大門,看見講台上坐了個女的,同時也安排我坐了一個位置,就像是一個演講用的會場。沒等我入座,我就發現有人要對我錄像,我順手把我的臉蓋住,我邊往出跑,邊喊著:「我不幹,我不幹。」我知道他們想陷害我上鏡頭,然後再強加別人的邪說,目的很惡毒。
有一天,省婦聯來了一男一女找我談話,這時我正在被關小號,頭都是暈的。我直接講我在遭受迫害,大法師父教我做一個品德高尚、利國利民、而且身心健康的人。我們知道自己沒有做錯事,所以那些酷刑、謊言改變不了人心,改變不了我們對師父、對大法的正信。這內在的變化,是來自內心深處的渴求。誰都不可能改變我們,只有真、善、忍才能改變我們。
一次,我所在小號的獄警們氣沖沖的來了,說:「你們法輪功怎麼還在天安門自焚啊?」我說:「那絕不是法輪功的學員,不要搞栽贓,那是魔幹的,那是在迫害大法。大法書中很明確的規定不能殺生。」我還說:「我們這麼多人被你們打,哪個人還過手?」
二零零一年的某個月,勞教所召集了各地「610」準備開「表彰大會」。當時我沒任何個人安危顧慮,我應該維護大法,清除邪靈!我在大會上高呼:「法正乾坤!」同修們也都齊聲高呼:「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
這次以後,株洲勞教所對我進行報復性的打針,我被長期的吊針灌食。在那個邪窩裏,警察每天想出各種殘忍之極的害人方法,想盡一切辦法要把人追求真善忍的信仰破壞掉。
被非法判刑、在看守所遭受迫害
二零零二年八月的一天,我從一位法輪功學員鄧果君(已經被迫害致死)家門口路過,她擺個長凳在門口坐著,招呼我進屋坐一下,我們幾年沒見了。結果被監控她的人誣陷為聚會,並舉報到了公安局。我和鄧果君被綁架到郴州市北湖區邪黨學校。就在路途中,北湖區「610」吳志強坐小車追上來了,問抓的是誰?當知道是鄧果君之後,惡狠狠的從車上抻出右手一揮說:「罰款一萬元!」
我們被非法關押在邪黨學校兩天後,又轉到各自的單位繼續遭受迫害。我又在單位賓館被單位專人輪流監視。過了大約一個星期,「610」吳志強和兩個公安來非法審我,大聲吼問大法真相資料的來源。他們又要我表態,寫東西放棄煉功。還說:「給你兩天時間考慮,否則就送到大西北去。」其中一個年輕人把我非法押送到了螺螄嶺看守所。
幾個月後,他們在北湖區法院對我非法開庭。到了法院,我一下車就被強行戴上手銬,我高呼「法輪大法好!」一個便衣警察在走廊上沒人的地方,對著我的臉猛打一掌,我被打的暈頭轉向,兩眼翻花,甚麼也看不見,因為扶著牆壁才站穩了。非法開庭時,沒有旁聽的人,我自己辯護。檢察官、法官一面之詞的構陷我。鄧果君被非法判刑三年;我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在看守所執行。
在看守所裏,我不配合做奴工,獄警就不開風門,並收走了電視機。十幾個人大小便都在監室裏,臭氣熏天。獄警這麼做的目的就是挑起同倉的犯人仇視我,不斷的折磨我。一次,我在外面風池打坐,當時正值冷天,一個吸毒犯提一桶冷水對著我的臉猛力一潑,當時我就像掉進水裏一樣嗆了一鼻子水,整個一身衣褲、頭髮都濕了。
有一次,小唐隊長搶去了別人傳給我的手抄本大法書。我絕食抗議,他們趁此機會野蠻灌食,選了幾個男犯人把我拖到走廊上,強行將我按倒地下,踩住我的頭髮,用鐵器從我的鼻子根裏往裏鑽。我大叫一聲,其中一個犯人說:「我就不怕你死。」並且立刻把婦科用的擴宮器插進我的嘴裏,用摻好的牛奶狀食物往我嘴裏猛倒。有個吸毒的人以為是牛奶,也想嘗一嘗。我看到有人使了一下眼色,她馬上就不嘗了。我知道,她們給我灌的東西都是有問題的。
很多法輪功學員的善行也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有良知的人。服刑期間,犯人們會對堅定的法輪功學員敬佩不已。記得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因為她們長期都在看法輪功學員煉功,她們覺的很好,她們全倉的犯人竟然集體和法輪功學員一起煉功,只有一個啞女沒有煉。後來我問她;「你為甚麼不煉?」她打手勢回答說:「我吸毒,天不允許。」以此來表達自己對法輪功和法輪功學員的敬意。
還有的犯人公開表示:「回去我也要修煉法輪功。」曾經有一名犯人因為聽信了中共栽贓迫害法輪功的新聞,害怕到睡覺的時候都不敢瞟一眼法輪功學員的床,也不敢看法輪功學員一眼,只能面壁著睡,才覺的安心。但是後來她竟然改口說道:「我認為法輪功學員是最可信、可靠、又善良的人。回家了,我也要學法輪功!」
以上是我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實,也是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對法輪功學員殘酷迫害的冰山一角。 朗朗乾坤,報應不爽。其實這些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人,被中共邪惡集團綁架,做出這些喪盡天良的事情,從而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未來,他們才是最可憐的人。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1/8/10/19453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