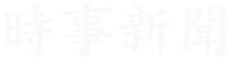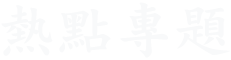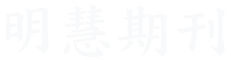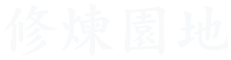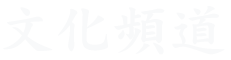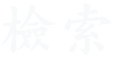紅塵夢醒
——一個青年修煉者的故事
我的姥姥、姥爺在一九九九年之前就煉法輪功。而我一直在邊上看著他們煉。當時還是比較小,對修煉沒甚麼概念,只是從本性上明白相信,第一次雙盤盤了四十多分鐘,從最表面上知道了一點法理。佛家有句話叫「佛光普照,禮義圓明」,那時我好像也沐浴在佛光當中,感覺很祥和美好。那時大法弟子們展現出來的境界和修為常令我感動和佩服。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集團開始公開打壓法輪功並殘酷迫害法輪功修煉者。姥姥給了我一小本大法經文,黃色封皮,大致意思是說這是很珍貴的,好好看就會有神奇展現。
我相信這書不一般,得好好學,也期待神奇出現。我就小心翼翼的收藏起來。但每當拿著這本經文使勁兒看時,卻怎麼也看不懂。後來被父親看到了,他很恐懼,就把那本小書撕了……
之後的日子,好像被塵封了一樣,為了學業忙碌著,為了考高分廢寢忘食,和萬千中國大陸的學生一樣在學校裏接受著黨文化的毒害,為了考學不得不主動接受洗腦,無神論、辯證唯物主義、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社會發展觀……如此種種,日日學、夜夜學、死記硬背。然而不知為啥每次考完試就忘得精光。
上初中的時候,與姥姥一起看了辛灝年先生的歷史講座光盤,我受到極大的震撼,原來真正的歷史是這樣的!
這對我日後對事情的判斷有很大的幫助。
上了大學,追求名利和情幻的路上越走越遠,在繁華的世界中彷徨、沉淪,慾望越來越多,患得患失,脾氣越來越大,貪圖享樂、只顧自己。我已經不是小時候那個我了。然而,不論身處環境多險惡,內心多絕望,總感到有種力量在努力的往回拽我,好像有一根線不能去逾越。
走近大法
從二零一零年開始,不斷經歷重重魔難:切身利益的失去、名譽上的各種謠言不斷、感情上的背叛、未來的迷茫、家庭的矛盾、做甚麼,甚麼不順,不明白為何這麼苦。
經歷著這些魔難,我開始思考人生,尋求生命的真諦。在此期間,姥姥也曾經希望我看看大法書,可我的心早已攪在紅塵之中,大法的書就是拿不起來。
在漫長的徘徊中,母愛是支撐我的最後一根稻草。然而母親當時卻罹患了癌症,真是天塌了!
在萬念俱灰中,我與母親雙雙拿起了《轉法輪》。最初的想法只是陪母親學吧。
我發現自己對《轉法輪》一點都不陌生,裏面的內容很多我過去都知道。隨著不斷學法和與同修們的接觸,我漸漸明白大法的珍貴。慢慢的我能從法上去看待身邊的事情,減輕了很多思想上的壓力和痛苦。
學法後,我面臨一次重要的選擇,當時我已經考上了外地某大學的公費碩士研究生,去還是不去念呢?我已經一心想修煉了,感覺師父在不斷往上推我,自身變化挺大的,如果去念書,意味著失去修煉的環境;如果不去,是走正修煉的路嗎?當時學法不深,很多事情看不透,最終還是去杭州上了學,走了三年半的彎路。下定決心在任何環境下都要修好,但經不住日復一日在常人的大染缸中薰染:出國遊學、國內各地遊歷、博物館、畫展、音樂會……一心撲在了藝術專業技能的提升上,在花花世界中又迷了眼。最初的激動在漸漸消失,每天堅持學法成了一種任務,執著心多的根本學不進去。但要讓我放棄大法,那又是絕對不可能的。
那時不懂真正的實修,陷在常人的慾望喜好中,沒有修煉中的切磋和對比,還覺的自己不錯呢。浪費了大把的時間和救人的機會,現在回想追悔莫及。
經歷這一切之後,深切體會到修煉環境對一個新學員來說太重要了。
走進大法
碩士畢業回到家,姥姥告訴我大法弟子在向北京高等檢察院和高等法院控告江澤民違法違憲迫害法輪功和殘酷迫害大法學員的事情。我當時覺的有點奇怪,「為甚麼控告江澤民呢?這不等著被抓嗎?」雖然不太懂,但這是師父叫做的,那我就一定要去做,我也要控告他!大家都在寫被迫害經歷,我沒甚麼可寫的,就照著法律條文抄了一遍,其實也不夠用心。過了些日子又聽說,本地訴江的信函在郵遞中途已被截攔下來了。
這時我正好要到北京去工作,就拿著對江澤民的控告狀送到北京高檢高法去投遞。警察說他們不收,只能郵遞。這樣我找到附近的郵局,寄了掛號信。為得到掛號信的回執,我留下了我在北京的暫住地地址。一直以來,我的修煉是非常的不精進,可以說是帶修不修的狀態,而當時自己卻意識不到。我是學藝術的,色慾這方面的業力比較突出,身邊不乏異性追求者,一直沒好好實修,到後期色慾心被加強了,學法也跟不上了。經常在房間裏看到小金星一閃而過,法理上知道是黑手,卻被干擾的無能為力。曾夢見自己留戀美景,而趕不上地鐵,不論自己跑多快,地鐵門都在我趕到的瞬間關上,車開走了……
到年底,工作上莫名的出現瓶頸,我最終選擇辭職,準備先回家休息。
辭職後沒幾天,有人敲門,說是社區對於外來人口身份證登記,我當時沒有任何經驗,就配合了他們。那時我思想上對中共迫害法輪大法弟子沒有甚麼具體概念。
之後一天晚上,有人敲我的門,三個警察一進來就到處蹓躂,當時我心裏有點懵,一個邪警說明是為我的訴江而來,問我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說,「對,我煉法輪功。」我不懂怎麼否定迫害,只是本能的感到修大法堂堂正正,我不能說我不煉。邪惡開始抄家,到處翻,我抱著大法書不給他,邪惡說給他一本就行,我一時糊塗就給了一本,現在才認識到絕不應該配合邪惡的,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能妥協交書。
之後他們又要書,我知道上當了,就死抱著不給他,他就開始搶,經過一番反覆撕扯,書還是被搶走了。我當時有所醒悟,這麼多年來,中共的野蠻行徑一直都是聽別人說,這次切切實實的發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其流氓的本質。
他們走後,我趴在床上失聲痛哭,內心知道這是色慾心不去被邪惡迫害,感到自己太差勁,打電話給家裏,正巧有同修在,我說,「我要去要書。」同修給予我正念支持,給了我很大幫助。我內心感謝同修,更感謝師父的苦心安排加持。心中久久難以平靜。關上燈,望著天花板,內心深深的被驚醒了,我徹底清醒了,我要好好修煉了。
第二天早上,我急切的想要學法,這回書都被抄走了,怎麼辦呢?想起一位同事在前段日子給了我公司的一個翻牆ID,好在還能翻牆,這樣我可以在電腦上在線學法。經過這一切,再一次看到法時內心感到非常珍貴和踏實。這一天是我的一個新的開始,我真正開始走入修煉了!
法理也開始不斷展現給我,原來過去我一直沒真正得法啊!這樣我上午學法,下午寫真相信,準備了十天。期間了解了法律,明白了這場迫害完全是非法的,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而訴江完全是一個公民的合法權利。在十天之後,拿著十多頁的真相信去派出所要書。
那天明顯感到師父的加持,沒有怕,走在街上,車裏的警察都向我豎大拇指,我知道是師父的鼓勵。等見到那天的警察,進了警務室,裏面煙霧繚繞,煙味嗆鼻,一幫警察在裏面聊天,該邪警拿著我的信給裏面的警察看,我滔滔不絕的斥責他們來抄家是非法的,我要拿回我的書!心情激憤,摻雜著爭鬥心、顯示心。我當時的心性標準就是那樣的,很多人心沒去。最後他們辯論不過,有個人說,帶她去拿書吧。
我起身跟著去拿書,這時看到那天的另一位去抄我家的警察滿臉擔憂的看著我,而我卻充滿歡喜的意識不到那意味著甚麼,天真的以為自己可以拿到書。
到了地下室我就被扣下了……
關進了牢房,失去人身的自由,密閉的環境,昏暗的燈光,對於未來的未知,這一切對於一個常人,精神瞬間會被壓垮。不斷的聽到有人在哭,在走來走去的精神不安,我卻心生一念,「師父,這不是我應該呆的地方,我今天就要回家!」
與我關在一起的女孩與我攀談。她是一個佛教邪悟者,說了些對師父不敬的謠言,我勸阻無效,選擇不予回應。邪惡企圖動搖我對師父的正信,但不可能。
我開始平靜下來,怎麼會被關在這裏?想到師父的法:「身臥牢籠別傷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靜思幾多執著事 了卻人心惡自敗」[1]。我靜下心來向內找、發正念,感到身體細胞都在震動,我可以體會到師父的加持,雖然我自修煉到現在甚麼都看不到,但我就是相信師父在我身邊。在那種邪惡環境中,邪惡不斷的往我的思想中打入不正的念頭。我知道一個念不正,都會被擴大執著從而被鑽空子,我發正念否定,解體邪惡,感覺很漫長……
師父把一些法理展現給我:「我給大家舉個例子,佛教中講人類社會一切現象都是幻象,是不實的。怎麼是幻象呢?這實實在在擺在那兒的物體,誰能說它是假的呢?物體存在的形式是這樣的,可是它的表現形式卻不是這樣的。而我們的眼睛卻有一種功能,能夠把我們物質空間的物體給固定到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狀態。其實它不是這種狀態,在我們這個空間中它也不是這個狀態。」[2]我悟到經歷的這一切看似很邪惡,但只是一種假相,並不是不可改變的。而我只走師父安排的路,其它任何安排我都不承認、都不要。
提審的警察一見我就說:「怎麼是這麼小的(法輪功)?」我記的師父說,「無論在任何環境都不要配合邪惡的要求、命令和指使。」[3]所以問我甚麼,我都說「我不想回答」,也不簽字,他們也不說甚麼。最後問我要補充甚麼,我說,「十二月一日××等三位警察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到我住所非法抄家,拿走了我的私人物品,這是違法的。」(大意)
中途又經歷了一次抄家,在師父的保護下,沒抄到甚麼。我問他們我甚麼時候能出去,他們告訴我三個出路:「要麼罰款、要麼拘留、要麼去看守所。」我心裏想,這些我都不承認,我就聽師父的安排。最終在晚上,他們讓我上了車,我不知道要去哪裏,旁邊協警女孩偷偷告訴我,「去看守所。」到了看守所,做身體檢查,我在想如果不合格就好了,但結果沒有任何異常。我提出,我要見管事兒的人。
他們把我帶到了一個審查案卷的工作人員面前,我告訴他,××等三個警察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到我住所非法抄走了我的私人物品,這是違法的。我到派出所要回自己的東西沒犯法。(大意)
等了很長時間,他們把我帶出了看守所,上了車,我以為沒事了,歡喜心又自己跳出來了。但卻得知是少了文件,還要返回來的。這時我心一沉,發現自己的腿在不由自主的發抖,怕的物質席捲而來……
這時突然想到,哎呀,我有師父呀,弟子就聽師父的安排!頓時一切怕都煙消雲散了…
一路我望著窗外,面沉似水。協警女孩說,「學法輪功的女孩怎麼不像普通女孩那麼活潑?」意思是我好像不接地氣。我反應過來,說,「我平時也和你們一樣,只是現在身處的情況,有點笑不起來。」其實現在悟到,當時還是在執著自己,還是在個人修煉之中,沒有像很多弟子那樣無論身處任何險境都能放下自我講清真相,我差的太遠。大法需要我達到那種不執著自我的思想境界,我沒達到。這時協警女孩說,「如果進了看守所,你的檔案上會有記錄,到時你就別想找好的工作了,一生前途就完了」。我沒有甚麼波動,曾經的我心比天高,而此時這些真的看淡了,微不足道。女孩又說,「看來你今天是出不去了。」我堅定的說:「我今天一定能出去。」這時女孩豎起了大拇指。而我內心知道,時時處處都是對我的考驗。
回到派出所,協警女孩給我接了杯白開水,我平靜的喝著。聽到一個年輕警察說,「人家真行,到了看守所還說自己沒有錯。」過了一會,他們說要「解除傳喚」,把我帶回地下室辦手續,再一次走在通往地下室的路上,歡喜心又出來了,此時想到師父的一段法:「我給大家講一個佛教中的故事:過去有一個人費了好大勁修成羅漢了。那人要得正果了,修成羅漢了他能不高興嗎?跳出三界了!這一高興那就是執著心,歡喜心。羅漢應該是無為、心不動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白修了得重修吧,又從新往上修,費了好大勁兒又修上來了。這回他害怕了,他心裏說:我可別高興了,再高興又掉下來了。他一害怕又掉下來了。害怕也是一種執著心。」[2]看來我真應該坦然不動才是,想著心也平靜了。
年輕警察拿出「解除傳喚」的單子讓我簽字,我不簽。他說,「我是信佛的,但是對於你們這信仰,我持保留意見。」說到此,我遺憾當時沒能切實講清真相,眾生就在我面前,我沒能救了他。協警女孩說,「簽吧,不簽是出不去的。別人都是簽這個出去的。」我看著單子上的內容:證明身份信息屬實;再就是證明警察沒有毆打被傳喚者。拿著單子猶豫著,知道不配合邪惡,可是這單子上寫的只是信息核實,沒有其它的,到底應不應該簽?這時年輕警察說,「你們不是修善嗎?你不簽字我們也得陪著折騰,你也得為我們著想啊。」當時還是法理不清,覺的是應該為別人想的,而且心裏希望出去,就簽了字。覺的不對勁,卻想不明白不對勁在哪裏。現在認識到,那是絕對錯誤的,等於承認了迫害,再說這哪是真正的善啊!那是害了眾生,讓眾生對大法弟子犯罪成為既成事實。
往外走,遠遠的看到曾經帶我抄家的警察,我揮揮手:「拜拜」,他面含笑意。走出派出所,看看表,將近午夜十二點。心中感慨萬千,充滿對師父的感恩,都是師父加持,沒有師父的保護,我能做甚麼呢?一分一秒都修不了。
一切從零開始
我回家了。師父安排了精進的同修來交流,我逐漸明白了甚麼是正法修煉。開始走入真正的修煉,過去的三年半,過去的一切都已過去,現在我的修煉從零開始。
真正開始修煉了,各種形形色色的魔難干擾接踵而來,有時尖銳的要過不下去了,體會到前所未有的苦和難,觀念被一次次的衝擊。過去對我很好的家人,突然對我不好了,矛盾不斷;工作上處處碰壁;另外空間的干擾不斷,雖然看不見,也能感到那種無形的壓力。
「一個是新學員,你修煉的那段過程和你證實法的這段過程是溶在一起了,要你攆上來嘛,所以個人修煉是伴隨著做證實法同時進行的。」[4]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在證實法,而我之前在修煉上是掉隊的,基本不懂實修,從新走回來,好多心要去,好多關要過的,證實法的路,一度沒做好。很多大法弟子方方面面都做的很好,在哪人都說他好,在哪都在證實法。而我一度相反,修煉後家人對我有意見,社會上處處受阻,甚麼都變的不好了,這還怎麼證實法?還給大法抹黑。
從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一七年末,記錄了兩本厚厚的修煉心得,後來發現修煉沒那麼複雜,逐漸簡單,就慢慢的不太記錄了。隨著不斷修煉,不知不覺中,很多心放下了,很多心看淡了,修煉環境也在不斷好轉,目前很多方面還沒完全正過來,很多方面還得切實提高,但明顯感到阻力逐漸少了。原來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走正師父安排的路,一切盡在其中。
每當修煉到一個新的階段的時候,師父會幫我安排新的修煉環境,與不同的同修結緣,證實大法。至此,我珍惜修煉的環境,珍惜同修間的緣份,也珍惜剩下不多的修煉時光。謝謝師父!
證實大法
最初一年,我走出去證實法主要是往居民樓裏送資料,光盤或者是小冊子,用塑封袋包裝好,貼上膠帶,裝進小包拎出去了。基本是進一個樓棟,發完後走很遠,再進一個樓棟。開始怕心還是很重的,一上樓還沒等發,心就開始控制不住的突突突的跳。我就開始念正法口訣,背師父的法。明顯感到當法學不好、正念不足時,干擾就比較大。例如,在中途就有人上下樓,有人開門……
一次剛發完就有人回家,看到門上貼的光盤,就毫不客氣的摔在地上;還有一次,我剛發完就有人上樓回來了,看到我下樓,知道是我發的,就把光盤朝我的方向狠狠的摔過來……我都默默的回去撿了回來,各種人心翻騰。開始幹事心是比較強的,後來提醒自己不是幹事,是證實法。所以再發的時候,儘量的保持正念,讓眾生得救。
也有時剛發完就有人拿回家了,還有的好像去串門,門沒敲開看到上面的資料,就帶走了。有一次正在發,旁邊的門開了,出來一個男的看到我,離的比較近,互相都愣了一下,我的心動了一下,轉而問他:「小冊子您看不看?」他說不看,就走出去了。還有一次,晚上在成排的露天走廊的樓上發,從一頭發到另一頭,到中間突然發現有一個男的一直在外面乘涼,在看著我,這把我嚇了一跳。他問我,這是甚麼呀?我遞給他一本,讓他看看,上面有真實新聞。他問我是不是街道讓發的,我說不是。當時也沒能坦然的講真相,怕心挺重,遇事本能的保護自己。
我悟到,自我是一個厚厚的殼,它的本質就是為私為我的,證實法的過程,就是不斷的突破自我,破繭而出的過程。
突破面對面講真相
一直以來,面對面講真相都是隨緣的,但是開口很難,總是繞來繞去的維護自己。修煉前我不善言辭,又內向,和現代很多年輕人一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從不主動與陌生人交談。現在意識到,不與陌生人說話的冷漠和防備是一種黨文化。而對我來說破開這層殼尤其難。
在二零一七年初,我有了面對面出去救人的心,就跟隨同修出門講。師父鼓勵我們,將有緣人帶到我們面前,有的人聽了真相很高興的。當然也有魔煉心性的時候。有一次特別不順利,聽到的都是不悅耳的話,被斥責,給白眼。有兩個女孩還沒等我們開口就往後躲,驚恐的看著我們……最終一個沒勸退,心裏承受不住回家了。
到家打開剛收到的快遞,看到賣家的贈品──一個金色的小粘貼,上面寫著「never give up」(永不放棄),我感到了師父的慈悲,悟到這是來自師父的鼓勵。
一天出去辦事,看到遠處一位阿姨在種菜,我內心感到那是有緣人。但執著於自己的事,想辦完事回來再來和她講。當我回來的時候,她身邊多了很多人,而我當時沒有那麼強的正念,機緣錯開了。
一段時間以來,已經好多次因張不開嘴使有緣人失去機會。恨鐵不成鋼,源自於內心深處的傷感,走在街上就抑制不住的大哭,回到家躺在沙發上哭。深深感到自身使命的重大,卻苦於無法突破開口,實在太難了!
師父看到我有救人的心,不斷的幫我。我跟著與講真相做的不錯的同修到了車站,看同修怎麼講。同修沒怕心、三言兩語就勸退一個,我當時根本做不到,在旁邊看著她講我心裏都有點緊張。後來跟隨一些同修去超市,跟了好幾個月,驚嘆於同修妙語連珠,我怎麼就學不會。自認為在人中算是有些文化的,一到講真相,好像智慧完全受阻,張嘴就不知道該說甚麼。期間,師父不斷把有緣人引導到我身邊,我從與人聊天開始,先不抱任何目地突破與陌生人說話這一關吧。只是單純的與人聊天還不能張嘴嗎?慢慢的我能坦然與人聊天了,也有些人做了「三退」。
出門偶爾能遇到一位曬太陽的爺爺,我曾與他講真相,他那時受電視毒害,雖然不信共產黨,但對大法也很抵制。可他每次見到我,還沒等我開口,他就開始擔心我,並絮叨一番:「小姑娘,幹點甚麼不好,我是擔心你……」我就開始接他的話茬講真相,但總感覺怎麼講也講不透,他總在重複他那一套。有時他好像明白了,再見面又不明白了,最後表現出不願聽了。後來我送他小冊子看,再碰到他時,他說被老伴兒扔掉了。二零一七年開始送台曆的時候,我想要不要送給他一份呢?最後想,還是給他機會吧。送給他時,他說,「這個有用,謝謝你姑娘!」拿著就走了。再見面時是下半年了,他主動跟我要二零一八年的台曆。這位老爺爺對大法的態度轉變了,也明白了。
通過這事,我體會到原來大法台曆有這麼神奇的力量。二零一七年末,我與同修又面對面送台曆,勸「三退」。慢慢說的多了,見面就是那套嗑兒,「叔叔(或阿姨),我們免費贈送台曆你要嗎?」有人會問「是甚麼台曆?」我說:「我們是修煉法輪大法的,給人送福,想告訴咱老百姓法輪大法是正法,不是像電視上說的那樣,咱老百姓別仇視佛法,那樣對咱自己不好……」有時說:「現在這事也不敏感了,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人修煉法輪大法,只有共產黨迫害打壓……」如果對方能接受,然後詢問,「請問叔叔/阿姨,您過去戴過紅領巾嗎?入過團嗎?入過黨嗎?」「全世界只有共產黨迫害正信,善惡有報是天理,咱老百姓別跟著遭殃。」「咱加入黨、團、隊的時候,曾舉手發誓要把一生獻給共產黨,但誓言是要兌現的,命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別許諾給任何人,過去發的『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誓言咱心裏別承認,要廢除掉。給您起個××的化名退出來吧。」又時有人會驚奇,「怎麼這麼年輕也煉法輪功?」我說:「就像信基督教、佛教、道教的不也有年輕的嗎?信仰甚麼不分年齡。其實修煉法輪大法的年輕人很多呀,在國外更多,很多都是有成就的、高學歷的。」
也有人說:「我不信法輪功,我只信我自己。」我說,「沒說讓你信,也不是讓你煉,就是告訴你別反對,因為反對佛法對咱自己不好。」這樣很多人都表示可以接受。
一段時間內,很多人都對我說,「這麼年輕,幹點甚麼不好非幹這個?」我還覺的奇怪,怎麼都跟我說這句話。後來意識到,哦,是我在工作中不夠用心了。
有時很多人都說,「管不了那麼多,管好自己就行了。」我認識到,看來是我有私心,在家庭中沒做好,只顧自己了。
有很多人問:「法輪功給錢嗎?」我想自己是不是有利益心了?
有時很多人問我,「你們師父在哪?」向內找發現原來自己還有不信師的因素。
講真相中動不動就有誇我長得漂亮的、要給我介紹對像的、要電話號碼的等等,我真苦於這色慾心啊,怎麼老也修不好。講真相是嚴肅神聖的事情,絕不允許這類事情出現的。
有時法學不好,講真相別人就不想聽,有個阿姨直接對我說,「姑娘啊,你的力量太小了!」
又一次,和一位叔叔講真相,他說:「怎麼沒看見有法輪功的人在車上讓座?如果讓完座說是修法輪功的誰都明白了。」(大意)當時我還辯解:「您怎麼知道法輪功沒讓座的啊,做好人好事的太多了。」突然意識到,對啊!這段時間我就因為私心沒讓座啊,原來是在說我!我對叔叔說,「哦,我知道了,您的意思是讓我實修對不對?」他笑著點了點頭。我笑著說,「好的,我知道了,我會實修的。」再一步步講下去,他最終「三退」了。
我體會到修煉太嚴肅了,任何小事在上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小事做不好,救人就出現阻力呢。
有時被不明真相的人數落,被譏諷,也是剜心透骨的。有一次,被一對夫婦譏諷,我站在那心沒動,旁邊一位男士來與我說話,最後了解真相做了「三退」。還有一次,與一位女士講真相,當說到共產黨時,她當場就炸了,很不理智,哭著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很有煽動性,還有人在圍觀看熱鬧。我正念有些不足,最後選擇離開,面子上真有些過不去。
只要有救人的心,師父就會不斷把有緣人送過來。有時走路的時候,有緣人就會站在邊上,就像在等著,過去一講就成了。講的多了,就好像會形成一種習慣,見人就想救,沒太多顧慮。
一直以來,不太願意和年輕人講真相,覺的現在的年輕人很冷漠,怕碰釘子。一次,我看到有年輕人過來,心想:年輕人怎麼了?年輕人也得救!甚麼都不想,就去講,他退了。發現給年輕人講真相勸「三退」也沒那麼難啊。也有沒講好的,有次和兩位女生講,一個女生低頭不語,另一個在點頭。我剛離開,就聽她倆一起笑道:「好尷尬呀!」我心想,我若不是修大法,我比你們還尷尬。隨著正法形勢的推進,最近感到三退沒那麼難了,有時看看「三退」名單,好像已經不少了,心中有個聲音說:「可以收工回家了!」我馬上否定,「救人還有收工一說嗎?眾生都在等著救呢,不做能行嗎?」有時覺的自己不錯的時候,就想,都是師父在做,是正法形勢的需要,我達不到要求還不行。
前幾天想要向一位叔叔講真相,他不理我。之後我與別人講,他在旁邊走來走去。我見他又過來了,我迎上去與他說話。他跟我說:「你知道我是幹甚麼的,我就專門管你們的。」說著拿出了證件,我心裏還是稍微沉了一下,說:「你在旁邊走來走去的,我心裏知道,但我是為了你好啊,不然也不會和你說。」他說:「你就像我孩子一樣,你離開吧,你們的材料我看了很多……」
走在路上,我發現怕心還是出來了,望著滿大街新安的攝像頭,心裏也打起了鼓。「考驗面前見真性」[5],看來自己的正念還是不足啊,修煉應該再下功夫。
修去對時間的執著
每次聽到有人說正法要結束了,我的心就突突的,挺著急,對時間還是挺執著的。一直以來我都不算很精進,安逸心較重,修煉不能下苦功。自身修煉、三件事做的還不夠,學法煉功還是干擾不斷。我得儘快做好啊,但覺的要突破還是挺難的。對於跟師父正法走過來的老弟子來說,修煉已經到了尾聲的尾聲,而對我來說,修煉的路好像剛剛開始走,太多的人心要去,太多的人要救,太多的事情要做好,太多的路要走。遺憾醒悟的太晚,修煉是有結束的那天,而我只能珍惜時間,再精進了……
有一天突然想到,應該從師父正法的基點上看問題,不能從自我角度上看問題。何時結束是師父正法的需要,對時間的執著是對師父的不敬。我就盡自己的本份,兌現誓約,不要執著自己。一路走來,我真心體會到修煉機緣多麼難得,深深體會到一個迷失在現代社會中的年輕人從所謂的「現實」中走出來有多難。雖然看不見,也體會到師父度我的艱辛和付出。雖然只有兩年多的實修路,話匣子打開,要說的實在太多了,師父給予我的太多了,內心充滿了對師父的感恩。
謝謝師父!
謝謝同修!
註﹕
[1] 李洪志師父詩詞:《洪吟二》〈別哀〉
[2]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3]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4]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三》〈大紐約地區法會講法〉
[5]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見真性〉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8/8/22/1716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