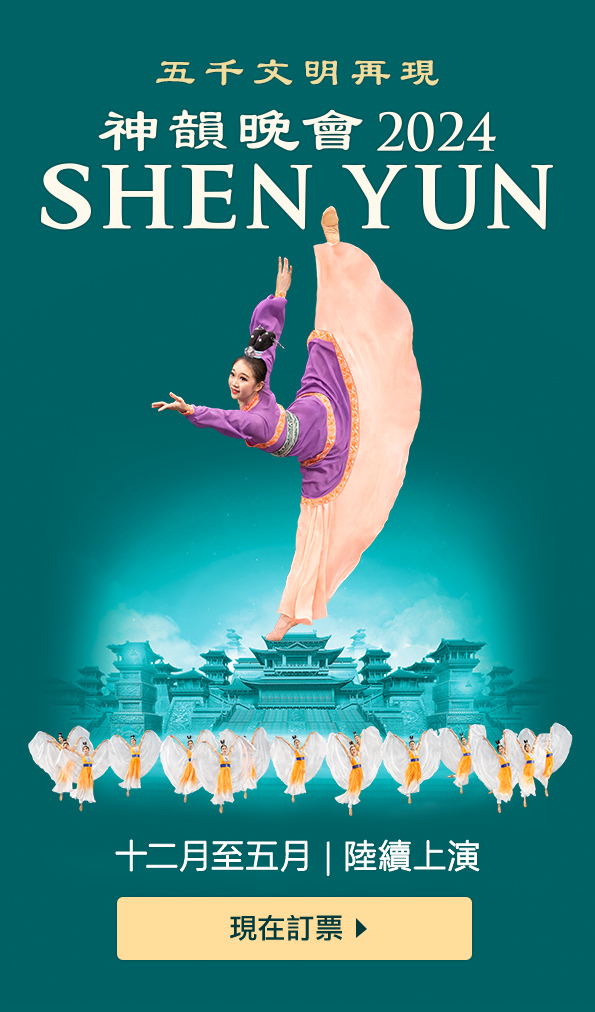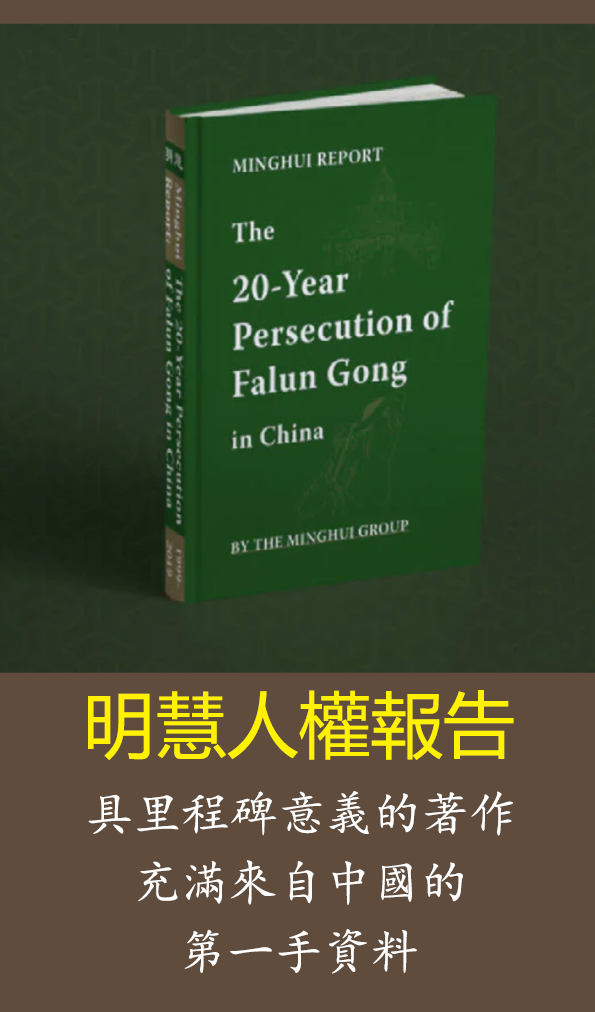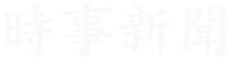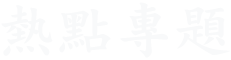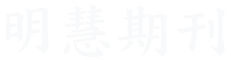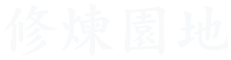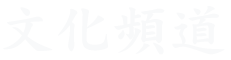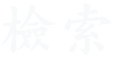寧夏藥店職工水雪芳所遭受的迫害
下面是水雪芳女士自述她的遭遇:
我叫水雪芳,今年五十七歲,原來是寧夏銀川市新城藥材公司新城大藥店職工。我十六七歲就得了甲減,一直服用含碘食物,因長期服用碘又得了皮膚病,二十八、九歲開始時常起風疹,醫院診斷為蕁麻疹,每當遇熱受涼就起的一片一片的,撓一下就癢的要命,手不能碰涼水,嚴重的時候腫的眼睛都睜不開。從一九九零年開始吃藥,連續吃了六、七年。因為長期服藥,帶來一系列的副作用,造成五臟六腑都不舒服。服藥有很多禁忌,不能吃肉類蛋類、魚蝦,又造成胃疼胃酸、貧血、頭暈、乏力,精神不振,老想睡覺。還時常腰疼,彎下腰起不來,立起來彎不下腰。
因為身體不好,脾氣也暴躁,丈夫不理解不忍讓,所以我倆經常吵架,和婆婆關係也不好;在單位和同事有矛盾吵架吵急了就動手(曾打過兩個同事)。那時,我對生活沒有一點信心了,但是因為孩子還小,自己的任務還沒完成,就只能痛苦的煎熬著。
一九九八年二月,一個了解法輪功的朋友看我皮膚病嚴重,就推薦說:法輪功祛病健身很好,給你《轉法輪》這本書你看看,這本書很好。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反覆看了三遍《轉法輪》之後,我身體的所有病症就消失,我真正體會到無病一身輕。後來我輾轉找到銀川市新城(現在更名為金鳳區)三角公園的煉功點。這樣就同時學法煉功,開始修煉了。
修煉後,我按「真、善、忍」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工作中不計較得失,不和別人爭鬥,工作認真,吃苦耐勞;能忍讓了,對以前打同事的事很內疚很後悔,想給對方道歉,但因單位改制,她們都調走找不到了;別人即使對我不好也不懷恨在心了。因為我的忍讓,家庭也和睦了,我對婆婆、對丈夫也不氣恨了;對利益也看淡了。丈夫看到我身心的變化,對大法很認可,每到學法的時間,丈夫主動提醒我,讓我趕快去。
一、說真話被綁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突然開始全面迫害法輪功。三角公園煉功點的人遭警察驅散,學法點也停了。二零零零年三月,要開「兩會」了,我就想到北京去找參會的人大代表,給他們說說我修煉法輪功祛病健身的經歷,讓他們給國家最高領導人反映真實情況,停止污衊法輪功、還我們師父清白,給我們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
三月一日,我和本地一個同修結伴到了北京。三月四日,在魏公村一個旅館裏,我們三個寧夏同修半夜被萬壽派出所的警察綁架到萬壽派出所拘禁。當時關押在派出所的寧夏法輪功學員有六七個,不分男女關在一間房裏,由警察輪流看守。關了幾個小時後,有人提出要上廁所,看守的警察就把我們不上廁所的人帶到另一個房間。這個房間用鐵柵欄隔成了裏外兩部份。這個房間的地面積了一層尿液,明晃晃的,人進出用磚頭墊著踩來踩去,無比臊臭。警察讓我們把這個房間的尿液清理掉,我們六七個人就用簸箕、桶子、拖把、報紙連舀帶拖,把地面打掃乾淨了。非法關押期間,警察提審我好幾次,提審時警察還污衊大法、污衊我師父。
六日,派出所警察將我們所有人押到寧夏駐京辦事處。他們通知了寧夏公安部門,由寧夏銀川市的警察把我們抓回來送到新城公安分局,隨後又送到銀川市看守所。在看守所我被非法勞教一年半,期間,我丈夫請客送禮花了一萬多元錢。我被非法關押四十多天後,辦了(所外執行)回了家。
二、在銀川市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我被關押在銀川市看守所期間,每天被逼迫幹勞工。看守所從外面用大車拉來殘破的輪胎片之類的,這些膠片裏有尼綸線繩。我們要把裏面的尼綸線繩從膠片裏拽出來,廢膠、線繩再回收,看守所把這活叫撕膠,每天每人分一堆。廢膠裏的線繩和膠粘的非常嚴密,沒有任何工具,就靠手使勁往外拽線繩,經常用牙才能把線拽出來,全身都得用力。
我幹到第二天手上就有勒痕、牙也開始酸疼。有的人大拇指、食指上勒的都是血口子。幹上一天撕膠的活到晚上渾身酸疼,動也不想動,幹不完不讓睡覺。
十幾個人擠在一個見不上陽光的小房子裏,吃喝拉撒都在這裏,擁擠不堪,晚上擠一個大通鋪,人多時只能側身擠著,根本無法翻身。吃的土豆湯裏的泥砂磣牙、沒有油水,每天中午晚上都是這個。如果誰不願吃土豆湯,可以買麵條吃,但是一碗麵就十塊錢,當時外面的面一碗最貴也就五塊錢。而且裏面商店賣的所有東西都比外面高出好幾倍。
所有被關押的人都要輪流值班,一夜不能睡覺,萬一打盹讓巡邏的警察發現就辱罵、粗暴的踢值班人員所在的監號的門,監號所有的人都被驚醒。值班期間發生意外的事情就讓值班人員承擔責任。過一段時間還有武警到各監號搜查床鋪、衣物,看守所的女獄警也同時將關押人員逐個搜身。
法輪功學員在裏面的處境就更慘了,不讓煉功、不讓說話、不讓提法輪功。如果不背監規、不穿號服警察就加重迫害。有一天,我和蔣紅英煉功被看守所值班的看見,報告了馬隊長(女),馬隊長把我從監號裏叫出來,在走廊裏搧我耳光、用腳踹我,把我嘴巴都打的流血了。蔣紅英被戴上了腳鐐,她絕食抗議後才去掉。
三、單位助紂為虐
我在北京被綁架後,單位就停發了我的工資。從看守所回家後,我找單位(新城藥材公司)經理王建軍要求上班,王建軍推諉不管。後來鐵東派出所的曹台慶給我們單位打了電話。單位給我安排了一個崗位,離家很遠,每月只給二百塊錢的工資,別人每月能拿上千塊錢,而且還要求我給單位寫不煉功的「保證書」。我堅決不寫保證,覺得工資給得太少就不想去幹。有一天在家裏,我丈夫(和我在一個系統)一聽我不願去幹,怒火萬丈,逼迫我寫保證。我不寫,他將我頭髮拽上,把頭往牆上使勁撞。我害怕他把我打壞了,惡人會乘機造謠,給大法抹黑,我一邊哭一邊寫了不煉功的保證。丈夫把保證書交給單位,我只好去上班了。
我在單位幹了一個多月,這期間新城國保大隊姓王的、鐵東派出所姓張的警察到單位找我,再次逼迫我放棄修煉。到了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九日,我們單位辦公室主任郝曉東帶著鐵東派出所曹台慶等四五個人到我家,幾個人進門後就開始亂翻,搶劫走了《轉法輪》等私人物品。然後讓我跟他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跟他們下樓後,他們將我推到一輛車上,直接就拉到寧夏女子勞教所了。
四、在寧夏女子勞教所遭受的迫害
在勞教所,每個法輪功學員都被安排有兩個「包夾」看管,無論白天晚上都跟在身邊寸步不離的監視;警察每天還給我們放污衊師父的錄像、寫思想彙報;長時間「坐小板凳」,我的屁股都坐爛結了疤;撿脫水菜,任務很重,幹不完不許睡覺;切活性炭、撿辣椒麵裏面的雜質、撿甘草。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勞教所排演文藝節目慶祝「五一」,吸毒人員排了一個小品是污衊師父、污衊大法的,剛開始我就打算站起來抗議,兩個包夾一左一右將我按到座位上不許動。過了一陣勞教所所長湯寧到現場來了,我就喊:不要迫害大法!湯寧扭頭出去了。當晚,姓馬的隊長指使吸毒犯逼迫我面壁,連續四五個小時罰站後我噁心嘔吐,他們才放過。
有一次我丈夫帶著兒子和女兒到勞教所看我,我兒子放聲大哭。
在勞教所,管教和管教指使的犯人每天花樣繁多的迫害手段和幹奴工對我身體傷害特別大,體重嚴重下降,臉都脫相了,又黑又瘦。
二零零一年五月九日,勞教所從寧夏白土崗子勞教所請來管教和已「轉化」的幾個人。這些人來後將所有法輪功學員分成幾個小組,一人負責一組。開始我不轉化,姓趙的隊長威脅說:你不轉化,就給你加教(延長勞教時間)。我違心地寫了「三書」,二零零一年七月回家了。
五、長期被騷擾迫害
回家後我不修煉了。過了不久,我身體開始難受,腰疼、又出現婦科病的症狀,還有一次暈倒在廁所,把前門牙都磕斷了兩顆。為了祛病健身,我再次拿起了大法書。
我回家後,派出所、居委會的經常到家騷擾。派出所的給單位施壓,單位又派呂富軍(鄰居)、姓白的門衛長期監視我。我的一舉一動他們都會給派出所和居委會彙報。有一次,我回浙江老家十來天,我家所屬街道辦事處的王斌就給我老家的街道辦事處(浙江省臨海市上江村)打電話,辦事處又給上江村村委打電話詢問我是否在我父親家。
因為派出所、居委會人員頻繁的上門騷擾,我丈夫和兩個孩子都非常害怕,我丈夫鼓動兩個孩子藏我的大法書。有一次,鐵東派出所的警察張先華(丈夫的戰友)又到我家騷擾。張先華走後,我丈夫就開始罵我,越罵話越惡毒,還說:我要和你離婚,我再也不願意跟上你擔驚受怕了。我一聲不吭,他罵急了,往我臉上吐唾沫用拳頭在我身上頭上一頓亂打。
二零零八年過年前,我和丈夫、女兒三人準備到丈夫的老家(寧夏固原市)探親。出我們小區大門時,姓白的門衛搭訕道:你們走哪?我丈夫回答說回固原。我們到固原的第二天,就有一輛當地的警車到我老婆婆家騷擾,我婆婆、弟媳婦、我女兒都到門口看情況,我女兒擋住他們沒讓進門。我從固原回到銀川,有一次路過北街派出所,看到該派出所警察畢德穎,我就責問他:我回固原你竟然派人跑到婆婆家騷擾,把親戚都嚇壞了。畢德穎還大言不慚的說:我是給他們安頓讓悄悄盯梢,不要驚動人的。說完就推開我,讓我趕快回家。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我因住房拆遷,到當地同修張桂芳家借宿,結果被銀川市金鳳區國保大隊的孫文革、戴春花等人將我和張桂芳的妹妹張芳、張桂芳的兒子王建軍綁架到黃河東路派出所,我們被銬在長條椅上。半夜我把手從手銬退出來後走脫。從那以後的兩年多,我一直居無定所。
從九九年七二零至今,派出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一直通過監視居住、跟蹤、監聽電話、上門騷擾等方式對我們進行迫害,家人生活在恐懼之中。二零一二年四月,我從浙江老家回到寧夏,所屬地居委會(現在金鳳區立交橋附近的富康小區內辦公)的袁永真(女),多次到我家騷擾。每次去我家態度蠻橫,一進門眼睛就賊溜溜的四處張望,問我還煉不煉?說我頑固等等。這樣的騷擾持續了四、五個月,直到當年十一月份我家拆遷搬家為止。
六、家人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被非法勞教後,我丈夫要照顧兩個上學的孩子(一個十七歲,一個十一歲),還要上班,壓力大的都承受不了了。他到銀川市公安局去問情況,市局的人推諉說:這是新城公安分局的人幹的,我們不清楚。我丈夫又到鐵東派出所打聽消息,警察給我丈夫說了一通污衊大法的話,又污衊我。我丈夫聽了痛苦萬分,在派出所嚎啕大哭。這是我從勞教所回家後,曹台慶給我說的。
我被非法關押到看守所以後,丈夫單位(寧夏醫藥公司)每逢開會,經理孫常蘭(女)和辦公室主任王會庭就在會上侮辱我丈夫。我丈夫回家對我說:如果會議室地上有個縫我都鑽進去了。所以每次開會我丈夫都坐在犄角旮旯裏,有時候他氣得不行回家再拿我撒氣。
我住的是單位的家屬樓,丈夫和孩子因我遭迫害被鄰居另眼看待。
二零零八年過年前我和丈夫、女兒三人準備到丈夫的老家(寧夏固原市)探親。第二天,一輛當地的警車就到婆婆家騷擾,把我婆婆、弟媳婦等親戚都嚇得夠嗆。
我丈夫對大法的認可、對我的支持,到迫害發生後對我百般刁難、打罵,污衊大法、污衊師父,這全是因為中共對法輪功的造謠宣傳以及株連九族的迫害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