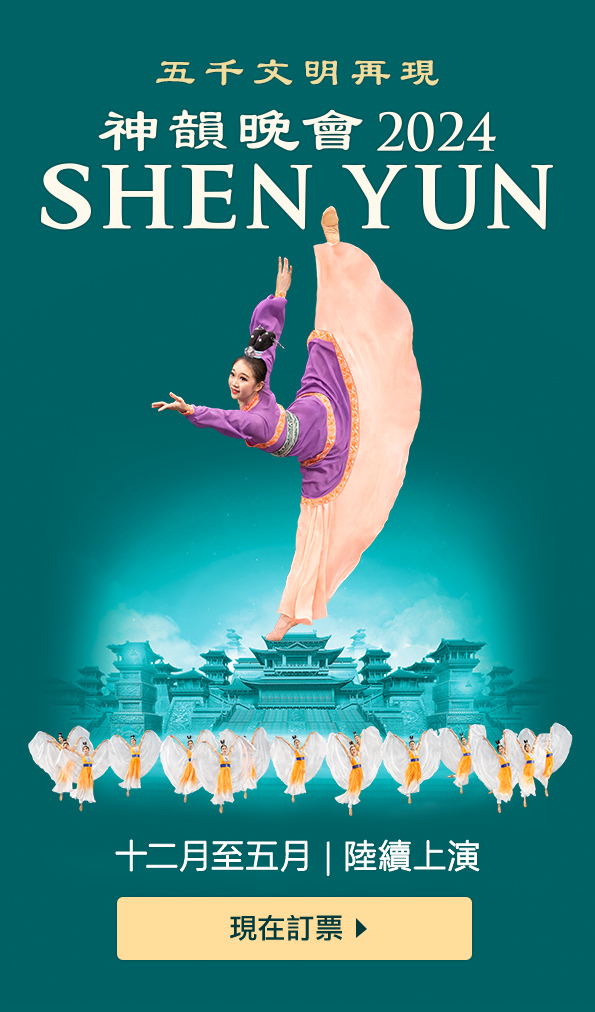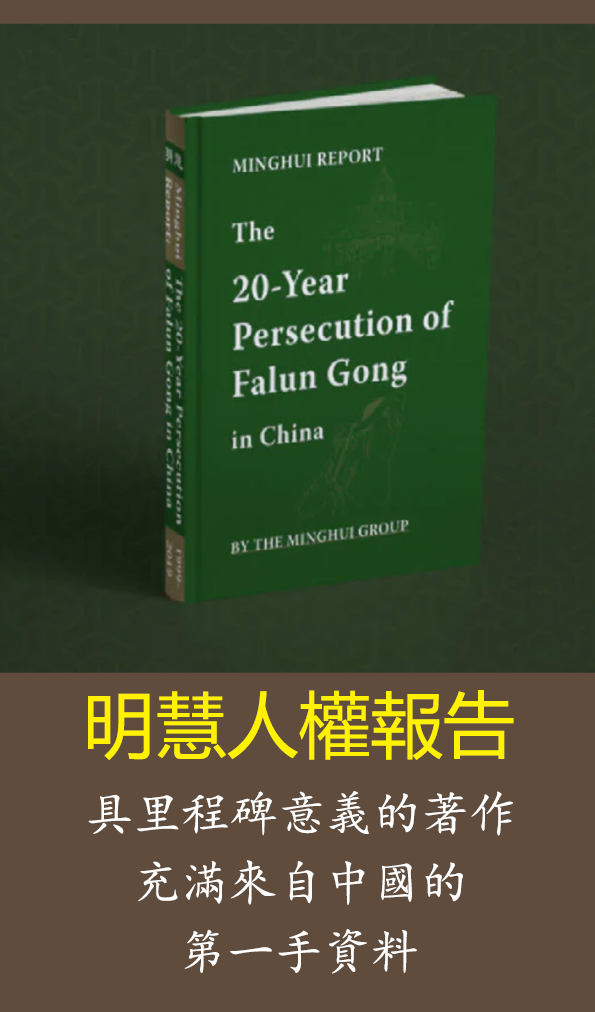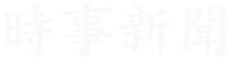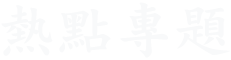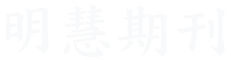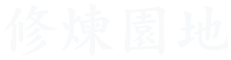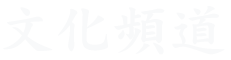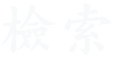十二年冤獄 一個個生與死的瞬間
——黑龍江省女子監獄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罪惡
 迫害前的裏書玉 |  被迫害後的裏玉書嘴、臉、肩膀歪斜,嘴角不自覺的流口水 |  被迫害後的裏玉書身體浮腫 |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被冤獄折磨十二年的昔日教委幹部裏玉書女士走出黑龍江省女子監獄,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家鄉阿木爾。如今,裏玉書回家已經三個月了,黑牢的傷害仍然使她生活不能自理。
裏玉書,今年六十五歲,在修煉法輪功之前,曾患多種疾病,修煉法輪功以後,她遵照「真、善、忍」做好人,所有疾病不翼而飛。裏玉書為人正直、無私,很有才華,寫的一手漂亮的毛筆書法,特別是隸書;她還擅長於刻章,不用草稿,隨手就刻,她的作品很受人喜愛。她憑著她的能力、實幹,受到林業局的重視,由普通教師升為校長、教育局主任,又提升為教育局書記。修煉法輪大法後,她不收別人的賄賂,不要學生家長的錢財,看到別人有困難,總是無償的幫助。
因為堅持法輪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九日,裏玉書和幾位法輪功學員被加格達奇公安局綁架,被加格達奇法院冤判十二年,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六日,關押到黑龍江省女子監獄。
裏玉書女士說:「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那裏沒有人權,沒有自由,我遭受了種種酷刑摧殘,惡警惡犯隨意的誣陷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我只能用我的生命去捍衛大法,捍衛我的信仰。」
裏玉書女士回憶:「面對慘無人道的迫害,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多次絕食抗議,最後一次絕食十年,遭到黑牢十年不間斷的野蠻灌食,每時每刻,我都掙扎在死亡線上,每次都是起死回生的奇蹟,使我今天還有機會向世人講述這個迫害,為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說句話。」
下面是裏玉書女士講述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裏一個個生與死的瞬間。
二零零四年:絕食之初──血淋淋的胃管
二零零四年三月初,法輪功學員張樹哲、丁玉等被警察騙走,關入小號折磨。其他法輪功學員們向警察講大法真相,我們是一群修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不是罪犯,要求放出小號折磨的法輪功學員,接著又有幾個法輪功學員先後被關進小號。小號內的法輪功學員開始絕食抗議,外邊的學員也在絕食響應,反對迫害。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日,我也開始絕食,警察用手銬把我們絕食的學員背銬起來,從早上五點到晚上八點,一直逼迫站著,晚上再把我們背銬在地上。就這樣,還時常打罵我們,或者把我們吊銬起來。
絕食初期,警察指使犯人商曉梅給我們下胃管,我經常看到從我口中拿出的胃管血淋淋的。商曉梅逼迫我放棄絕食,說:「長期下去,你的胃粘膜受不了的。」
當然,我絕食不是目的,是希望中共停止迫害法輪功,順應宇宙「真、善、忍」大法。多次灌食後,我的鼻子、食道、呼吸道裏邊都已經傷痕累累;每個犯人下胃管時,都感到太難了,經常要下十幾分鐘才能下進胃裏。
 酷刑演示:用開口器強行灌食 |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惡警大隊長鄭傑過來,把我手銬打開,又將我單獨關押一個地方,由犯人宋立波等三個人看著我,逼我放棄絕食。我繼續絕食反迫害,宋立波說:「那你這絕食就遙遙無期了。」是的,惡警、惡犯從此開始每天三次給我下胃管,連續了十年。
在這兒,我被迫害了一個星期後,惡警們看沒啥效果,沒有改變我堅強的意志,他們又把我劫持到了九監區。
九監區:一次次死裏逃生
當時,九監區迫害法輪功學員極其殘忍,「轉化率」(註﹕「轉化」就是被逼迫罵大法、罵師父,放棄大法修煉)最高,其它監區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都被劫持到這兒,具體實施「轉化」迫害的惡警賈文君,因此提了科長,當上了「轉化」迫害大隊長。九監區,每個警察都參與了迫害法輪功學員。而詐騙犯吳湘芬,不到三十歲,心狠手辣、詭計多端,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犯之一。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九監區惡警賈文君領著吳湘芬、劉鳳玲、高福豔等四個惡犯包夾,把我劫持到一幢空樓的一個空屋子裏,窗戶、門都有紙糊著。吳湘芬足足罵了我三天,然後,對我慘無人道的灌食。
吳湘芬騎在我身上,揪住我的頭髮,犯人李明英用手像鉗子一樣,捏住我的鼻子,劉某某用塑料瓶子伸到我的咽喉部位,隨時都有灌進氣管的可能,我的鼻子被掐破了。這樣,灌我幾天,每次灌一、兩個小時。
有一次,吳湘芬準備一個塑料瓶子,蓋上扎幾個眼,灌食時,裝上液體食物,將瓶子伸到我嘴的深處,咽喉部位。為了防止我吐出來,她用毛巾捂住我嘴,憋的我喘不上來氣,每時每刻都有灌到氣管死亡的可能。我的頭只要側一點,掌握到角度,我就可以調整,避免食物流到氣管裏,但是,她們不給我這個機會,按頭、捂嘴。有幾次,我猛一翻身,避免了生命危險。
當時那種瘋狂的灌食,簡直就是殺人!吳湘芬看我翻過身來,氣的她把瓶子摔了,說:「下回多放鹽。」
每次灌食近兩個小時,灌完後,我累的氣喘吁吁,每次下來,我的臉都被掐破了,臉、鼻子變形了,腫的、破的,青一塊紫一塊的。有時,給我灌的食物裏一次放一斤鹽。
後來,犯人鄭冬梅拿胃管來了,取代了塑料瓶子。吳湘芬揪住我頭髮,騎在我身上,胃管下到氣管裏,憋的我喘不過氣來,臉憋紅了。我說:「插氣管裏去了,憋死了!」鄭冬梅說:「你不是要死嗎!」說著,抽一管子(特大號注射器)食物,向給我灌食的管子裏推擠。我用力掙脫,吳湘芬死死的按著我,不容我動一點,看來,這次我無法逃脫死亡了。
一管子奶粉推進後,嗆的我一點兒也受不了了,一口鮮血帶著奶粉全噴出來了,我氣管裏沒存留一點食物,我又一次死裏逃生!第二天、第三天,她們又把管子插入了我的氣管裏,我掙扎著……
二零零五年:監獄深處的小號刑房
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晚上,九監區大隊長燕玉華來了,說:「快過年了,你再堅持絕食,就上小號,給你一天時間考慮一下。」第二天,她們把我綁架進了小號刑房。
小號潮濕,陰冷,只有走廊有兩組暖氣,暖氣漏水,樓上的暖氣也漏水,從棚上漏下來的水,就像下雨一樣,無處躲。床板很濕,被褥都長了毛。
小號有五個酷刑間,每間都有幾個法輪功學員被關在裏面,有的被關在小號半年多了,棉衣長了毛,手腳凍壞了。我被關在小號2號酷刑間。
3號酷刑間的法輪功學員給我背師父的法,我長期被獄警隔離迫害,學不到大法,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多學點法,可是,警察又把我弄到1號酷刑間,我聽不到同修背法了,我就高聲背師父的詩詞《洪吟》,包夾極力阻止,把1號酷刑間門關上。
1號間是個重刑間,有地環,雙手、雙腳銬在地環上,我被雙手銬上後,身體坐著直不起來,躬著腰,兩胳膊不能活動一點,控的非常難受。我一分鐘、一秒鐘的熬著,到晚上,他們還不給我打開。那些天,每個值班警察接班時,都先看我走沒走,看到我那樣虛弱的身體,怕我死在那裏,馬上給監獄裏打電話。
我在小號被折磨了四十天。
二零零五年:病號監區利用親人施壓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病號監區警察和犯人把我劫持走了,四個包夾,在一個空樓,每層樓沒幾個人,窗戶、門都用紙糊著,外人不准進入,裏面人不讓交往,也是被隔離迫害。
監獄把我哥哥找來,簽字,意思是我絕食死亡監獄不負責任,我如果死了,家人不要找監獄。我哥哥當然不會簽字,監獄搞了多方面的造假材料,有錄像、有記錄,我一旦被她們弄死了,她們好拿著假材料,推卸責任,造謠。我不配合她們做假。
過了幾天,監獄把我丈夫和我兒子也找來了,想利用他們「轉化」我,讓我放棄修煉,我向他們講,我為甚麼絕食,他們理解我,沒有對我施加壓力,我很感謝他們。
二零零五年:病號監區包夾──相淑芬、單玉芹、王新華們
監獄在全監獄範圍內找來了方方面面的人來迫害我,逼我放棄修煉,後來換了兩個包夾──相淑芬、單玉芹。
單玉芹,五十多歲,她自己說:不學無術,從小就和男孩子在一起玩打仗,當過兵,當過包夾。單玉芹經常毒打我,一次,她把我毒打一頓,妄圖踩斷我的胳膊、腿。經她踩完後,我手、胳膊不能伸,腿不能走路。
下午,他們又把惡犯王新華調過來包夾我,一天早晨,王新華把我按在床上,用笤帚扎我的臉,扎了一個小時,一個笤帚都紮零碎了,紮的我滿臉是血眼,滿臉是血,腫了起來。
王新華給我灌食,根本不把我的生死放在眼裏,野蠻而瘋狂。一次,她用一袋或半袋鹽,灌一半剩一半,揚在我身上。我的棉衣、內衣都濕透了,被褥也濕了。在我換衣服時,她趁機把窗戶打開,立時,北方十二月冒著白煙的冷空氣吹在我身上。
監獄裏搞很多假材料,達到他們即使殺了人,又把責任推給被害者,監獄還找過我們家人簽字:她死了,與監獄沒關係。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三日,犯人商曉梅說:「你簽個字,意思是你被灌死了,是你不配合,你要簽字,你配合我們。」我當然不會配合,為了留下我的死亡是她們野蠻灌食造成的這個證據,我就寫了個條子。
犯人包夾們繼續用婦科擴宮器給我灌食,那就是殺人,比屠夫殺豬還殘酷。單玉芹,騎在我身上,用勁擰住我的胳膊,還有按頭的,有按腳的,按臉的。王新華,用勺子或筷子撬開嘴,商曉梅將婦科用的擴宮器伸進我嘴裏,放到極限,嘴撐的簡直受不了了,每秒鐘都難以堅持,每次都灌一、兩個小時。
她們用勺子或大號注射器,將勺子送到我嘴的深處,隨時都有灌到氣管的可能。有一次,灌到氣管裏去了,我一邊喊,一邊猛用力一吐,不知哪來的那麼大力量,吐出去了。單玉芹馬上鬆開我,說太危險了,就鬆開了。王新華、商曉梅還告訴其他犯人:不聽裏玉書喊,按住她,不給她機會。我經常被嗆的受不了,她們根本無視我的死活。
我的嘴裏被擴宮器、勺子搗的非常痛,我已經沒有能力再抵抗了,那時我身體很虛弱。她們一方面在灌食中對我下毒手,一方面晝夜不讓我睡覺折磨我,將我雙手背捆著,兩條腿綁在凳子上,我睏的直摔跟頭。單玉芹每天把我雙手綁在凳子上,一坐就是十四、五個小時。
袁安芬,殺人犯,身強體壯,心狠手辣。一天晚上六點,我按法輪大法的要求立掌發正念,袁安芬跑過來,把我推倒在地上,她一腳踩在我身邊的小凳子上,「啪」小凳子碎了,第二腳踩在我的臉上,我喊:「法輪大法好!」她把褲頭塞進我嘴裏,兩腳在我臉上踩,我的臉立時腫了起來,頭上起了三、四個大包。我接著發正念,她用刷子柄打我的手背,頓時,我的手腫的像饅頭一樣。
我心裏只有大法的教導,我是在做好人,我不是罪犯。她們看我不配合她們,就利用灌食之際,往裏面放大蒜,辣的我受不了。一天,相淑芬被院長趙英靈找去了,給她下了死令:再發現裏玉書發正念,就扣所有包夾的分。這樣,她們就白天晚上不睡覺的折磨我。
她們熬的受不了了,相淑芬說:「老裏呀,不給你放大蒜了,你睡覺吧。」我說:「你說話算數嗎?」她一再表示,不放蒜了,我才躺下來,她們真的不放蒜了,她們給我「約法三章」,不准和其他法輪功學員說話。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在法上交流,必須破除這一邪惡的規定,我經常去其他法輪功學員監舍床上坐一坐,包夾們經常把我拖走。
一次,袁安芬猛的推倒我,我腦袋摔了幾個大包,屁股疼的很厲害,一年多不敢坐著,骨頭受到了損傷。那年大年初二,我闖進其它監室看看其他法輪功學員,相淑芬把我推回來,揪住我的頭髮往暖氣管子上猛撞十幾下子,撞的我頭嗡嗡的,滿頭大包。
一天早晨,我堅持發五點鐘的正念,打蓮花掌,住在我對面的惡犯何穎傑,一大步走到我跟前,抓住我左手大拇指,用力向外一撅,只聽「喀嚓」一聲,骨頭折了。我仍然打蓮花掌,她愣半天說:「人若不怕死,誰都沒辦法。」
二零零五至二零一三年:和屠夫殺豬無異的灌食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副院長趙慧華,眼看著她們對我這樣瘋狂、野蠻的灌食。王新華用筷子扎我舌頭,用勁太大,筷子扎折了,王新華就使用這個折的筷子碴,再狠狠用力往我的嘴裏猛一按,折的筷子碴扎入我舌頭很深,疼痛難忍,鮮血直流,流了滿地血,王新華馬上用衛生紙蓋住。
第二天,我舌頭、滿嘴非常痛,就是這樣,她們也沒放過我,她們還是慘無人道的繼續對我灌食迫害。灌食時,我滿嘴疼痛,無力抵抗。幾年過去之後,一提起當時灌食的情景,就連惡人商曉梅都深有感觸的說:「那真是生與死的浴血奮戰!」我在中共和它的犯人的魔掌下,還能倖存下來,簡直就是奇蹟,是堅信法輪大法的奇蹟。
從二零零五年到二零零六年兩年時間,幾乎是兩、三天,甚至更長時間灌食一點,商曉梅有時似乎很擔心的問我能不能挺住。王新華一直想餓死我,她對我能活下來,是非常的不可思議,懷疑我偷喝水了。那時我的體重也就五、六十斤,身體很弱。一次,商曉梅測我血壓,50~60,抽血化驗,血管裏沒血,商曉梅說:「老裏,這回你可完了。」她們看我身體虛弱,反而更加的迫害我。
二零一二年,因為我經常喊「法輪大法好!」包夾向警察獻「計」說:「兩天灌一遍,看她還有勁喊不喊?!」結果有一個月時間,兩天灌一點點。
二零一三年的一天,犯人谷雅茹來給我下胃管,她下一會兒,沒下進去,就非常氣憤的罵我,她越生氣,就越下不了。管子在我鼻子裏打折了,她再往裏推,疼的我已經受不了,因為管子打折了,食物灌不了,拔出來,從新插,撥不動,就像釘子釘在木板裏一樣,她雙手用力,往外拽,也拽不動,拽出來了,她再瘋狂的往裏下,邊下邊罵我邊打我的頭,那次插了五十分鐘,連我的包夾都看不下眼了去報告給了院長。這種折磨無異於一個屠夫對付一隻面臨屠宰的豬一樣。
二零零六年:院長趙英玲指使不讓睡覺、「五馬分屍」酷刑
一天,院長趙英玲來了,給相淑芬一本誣陷大法的材料,讓相淑芬給我念,我不聽,我大聲背《洪吟》,相淑芬生氣的走了,把王新華調來,當我包夾。
她們給我放誣陷大法誣陷師父的錄像,把我雙手背著綁在凳子上,電視機離我半米遠,放最大音量,我閉著眼背誦大法,這樣每天早七點到晚七點,持續一個月後,迫害又升級了。她們從惡警那兒回來說:「你必須吃飯,穿囚服,放棄修煉,服從獄警,否則你不能睡覺。」
不讓我睡覺,前兩天,我能挺的住,第三天我困的受不了,坐在小凳上,不斷的往地上摔,王新華為了達到不讓我睡覺的目的,準備了一盆涼水,兩個大號注射器,她們坐在床上,往我臉上哧水,我的衣服都濕透了。
第四天,六一零的科長肖林來了,我揭露她們不讓我睡覺,肖林公開慫恿她們,還罵我。
 酷刑演示:五馬分屍 |
 酷刑演示:五馬分屍 |
王新華經常用膠帶纏住我的身體,再把我「五馬分屍」狀吊起來,我感到很憋氣,手被勒的發青。一天晚上,王新華告訴單玉芹,把我捆起來,再用膠帶將我和放電視機的簡易桌子連上,我一摔跟頭,就帶動桌子,我離桌子很近,桌子一倒,電視機就砸在我身上。她們都上床睡覺去了。相淑芬哭咧咧的逼我說:「老裏,你就簽了吧,趕快簽字,簽了字,就上床睡覺。」
第六天晚上,王新華坐在床上,激將單玉芹說:「你老單不是有兩下子嗎?也沒制服她,你還是打人不疼。」單玉芹被激怒了,走到我跟前,猛勁抽打我耳光,左右開弓,打了十幾個大耳光,又拽我耳朵。
這時,王新華運足了力氣,一大步竄到我跟前:「啪!」一個大耳光,打在我左臉上,就像一塊巨石,從天而降,砸在我臉一樣,我感覺骨頭像裂開了一樣劇痛。過了幾天,別人說我臉歪了,我照鏡子一看果然歪了。我已經七天六夜沒有閤眼了。
六月二日,相淑芬、王新華又逼我坐小凳子聽她們念誣陷大法的材料,我不聽,也不坐。
二零零六年:遭毒打 生命垂危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我第四次被隔離迫害,我被劫持到監獄四樓警察辦公室,包夾是袁安芬等兩人。我是大法弟子,我堅持煉法輪大法的功法,袁安芬找大隊長於英民要增加包夾,於英民把王新華找來了。
七月十日晚六點,我立掌發正念,王新華過來打我耳光,把我打倒。我就大喊:「法輪大法好!」她邊打邊問,還喊不喊。她打累了,就用衣架往我臉上、頭上使勁抽打,衣架被打碎了,足足打了我一個多小時,我感到就像骨頭裂開了一樣,疼痛難忍,袁安芬回來了,她們兩個一起打我,我被打的昏迷不醒,神智不清。
那一宿,我頭疼痛難忍,我昏昏沉沉的呻吟著,早晨小便時,發現褲頭上有大便,不知甚麼時候便的,我的臉到處是傷,變形了,很嚇人。
王新華極力的封鎖消息,把我看的緊緊的,怕把我打成垂危的情況透露了出去,甚至連警察都不讓進來。我經常喊,王新華怕消息傳出去,經常趁袁安芬不在時,對我暗下毒手,她試圖撅折我的胳膊、腿,邊打邊問我:「我打你了,你說不說。」我告訴她:「說。」王新華經常恐嚇折磨我。
我經常高聲背師父的詩詞《洪吟》,背《論語》,我每次背大法時,王新華、袁安芬就把我按倒,用毛巾堵住我的嘴。有一個冬天的晚上,王新華把我光著腳拖到衛生間,把窗戶打開凍我。一天,袁安芬沒在屋,王新華把我打到地上,惡毒的撅我胳膊,還問我:「我打你,你說不說,說,我就撅折你胳膊、腿。」她還經常把我倒立起來,捉弄侮辱我。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醫院院長趙英玲和病號監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惡警馮雪來了,看我滿臉是傷,痛罵我一頓,罵我不放棄修煉,軟硬不吃,不服從監獄的邪惡管理,堅持煉功,她氣憤的邊罵邊用書打我的臉:「我們都在享受人生幸福,你在遭罪,我們給你灌食就是禍害你……」
二零零七年八月,獄警給包夾蔡琳(三十一歲,長的人高馬大,一米七的個子,一百八十多斤)、袁安芬拿來束縛帶,我煉功時,修淑芬將我捆綁上,因為我身體瘦,綁不住,修淑芬又將束縛帶增加了扣眼,再將我綁上。我煉功時,蔡琳和袁安芬就將我捆綁在床上。
 酷刑演示:罰坐 |
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我被劫持至病犯監區的十三組,我發正念或煉功,蔡琳就騎坐在我的身上,蔡琳的胖身體壓著我,我感到呼吸都困難。蔡琳經常喪盡天良的毒打我,許多有良知的刑事犯看到,都於心不忍,規勸蔡琳,蔡琳不聽。她像惡魔一樣抓住我,憤怒地往地上摔,摔的我滿腦袋大包,身上的傷不斷。蔡琳抓住我的腿,在床邊使勁的壓。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大隊長戴瑩領一幫犯人打手,突然闖入我住的監舍,把我所有物品翻看一遍,經文被拿走了,我的衣服都寫上犯字,下令法輪功學員不能同時在衛生間、洗漱間,犯人洗漱上衛生間也得安排批定時間,她們把「攻堅」大隊的管理辦法使出來了,想把病號監區管成閻王殿一樣。
我有針對性的破除這種迫害,經常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在衛生間、洗漱間相遇,甚至到其他法輪功學員監舍去。我經常被她們拉出來,每天警察上班,我都向她們喊:「法輪大法好!」
一天,戴瑩把犯人組長趙麗娜找去了,罵她一頓,給她施加壓力:「我再聽見裏玉書喊或從她那裏翻出經文,就扣全組二十幾個犯人的分。」趙麗娜回來後傳達戴瑩的意思,全組二十幾個人,個個魔性大顯,把我的東西又翻了一遍,被褥拆了,到處寫上犯字,把我按倒在地捆綁上,用膠帶纏上我的嘴,用腳踩我。趙麗娜把我用膠帶纏起來,捆上吊了起來。
那天晚上開始,獄政科長鄭傑來點名時,這是哈女監最緊張的時刻,有的犯人報數時聲音小點都要挨罵。為了反對迫害,我就選在這個時刻高喊:「法輪大法好!」那些包夾、組長、犯人討好警察罵我,打我,恨不得一下子把我打死、打服,包夾邵忠燃、趙麗娜魔性大發,狠狠的用盡全身力氣打我耳光,把我按在床上,發瘋似的下黑手。
二零一二年:不穿囚服 遭毒手 家人十幾年不得見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午,大隊長趙曉帆帶領一幫犯人打手把我硬拖到醫院住院處,讓包夾給我穿囚服,穿上後,把我用膠帶捆了起來。
一天,獄長白英賢來了,查看310獄房,中途,李榮利就打我耳光,不一會兒,來了十幾個身強力壯的犯人,強硬給我穿囚服,我拼命掙扎著,從床上滾到地上。惡犯高福豔,四十幾歲,身高一百六十五公分左右,體重一百六十多斤,她用腳踩我小腿,又用手擰我大腿內側,揪住我頭髮往床欄上撞,每天暗下毒手。她還把束縛帶往裏打個眼,緊緊的勒住我的雙手。高福豔回監舍說:「裏玉書哪來那麼大的勁,就憑她的體格,動彈都很難!」
一直到七月末,她們野蠻的硬給我穿囚服,有的人就遭惡報了,高福豔身體患病,到醫院針灸疼的她嗷嗷直叫,對法輪功學員迫害太惡毒殘酷了,老天發怒了,一天都下雨,雷聲、閃電,在監獄裏迴響著,有人看到火球進了屋,監獄的電視都擊壞了。
我不穿囚服,十幾年沒見過親人,我的親人千里迢迢,有的七、八十歲,來一趟,也不讓我見。
二零一三年:隔離關押迫害 常伴「法輪大法好!」
二零一三年八月,因為我總喊:「法輪大法好!」他們又一次把我第七次隔離關押起來。副獄長史耕輝、大隊長戴瑩、院長趙慧華硬把我綁架到監獄醫院住院處,那裏有幾個法輪功學員已經被隔離關押一年多了。我去醫院時,我的被褥都被她們拆散了,衣服也沒了。包夾郝丹君舉手就打我耳光,張口就罵,我要上衛生間,不讓我去。晚上我挺不了了,要小便,她們不讓去。
醫院那個環境,上廁所、洗漱都在她們的控制中,我要破除這種迫害,經常喊:「執法犯法,私設小號,迫害好人。」我要求見駐檢官員,揭露她們迫害法輪功學員、私設小號的犯罪行為。惡犯王微氣的把洗漱用的一盆水潑了一地,濺了我一身。她用盡全身力氣打我耳光,她打著我,我就大聲喊,直到她打累了,才停下來。
醫院那個地方是獄長經常去的地方,也是上邊領導來必去的地方,我經常喊:「法輪大法好!」揭露她們。邪惡是怕曝光的,她們不願讓我在那裏久住。一天,他們讓我離開醫院,把我劫持到了十一組。我看到了其他法輪功學員,說句話,惡警王某指揮犯人,把我拖走了,惡犯們很氣憤的把我的頭往地上一摔,我的頭磕破了,流血不止,按也按不住,她們把我抬到醫院縫了五針。
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我因為不放棄信仰法輪大法,被劫持關押了四個監區,綁架小號酷刑一次,隔離迫害九次,背銬九天,七天六夜沒閤眼,背銬在水泥地上,四個月不讓睡覺,遭到十年不間斷的野蠻灌食。黑監獄以「扣分加期」等條件要挾利用形形色色的犯人殘害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裏玉書出獄一個月以後仍留有被灌食的傷痕 |
出獄一個月以後,我身上仍留有被灌食的傷痕,這是外部能看到的傷痕,但是灌食主要傷在內裏,在呼吸道、食道、鼻道、胃等部位。
就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我出獄的當天,監獄惡警們也沒放過我,還是對我進行了野蠻灌食。我出獄一個星期後,突然半邊身子不會動,嘴、臉、肩膀歪斜,嘴角不自覺的流口水,從舌頭一直到下巴都發木、發麻,不好使,耳朵聽不太清楚,眼睛也看不太清楚東西,身體浮腫,得兩個人抱著穿、脫衣服,抱著上床。
我及親朋好友都懷疑:黑龍江省女子監獄在我臨回家的當天灌食中,給我灌了損害身體的藥物。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4/10/5/146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