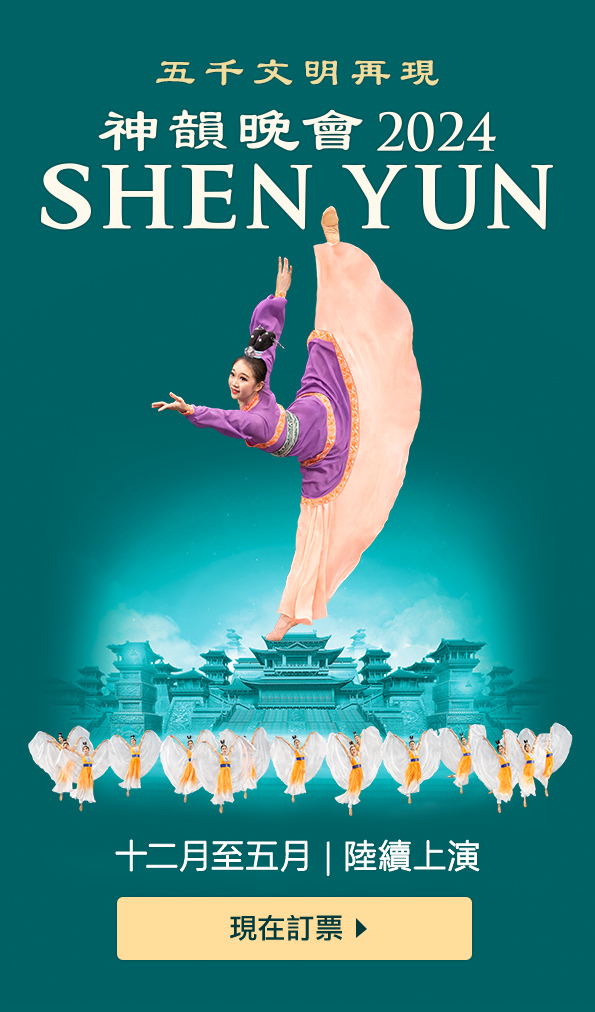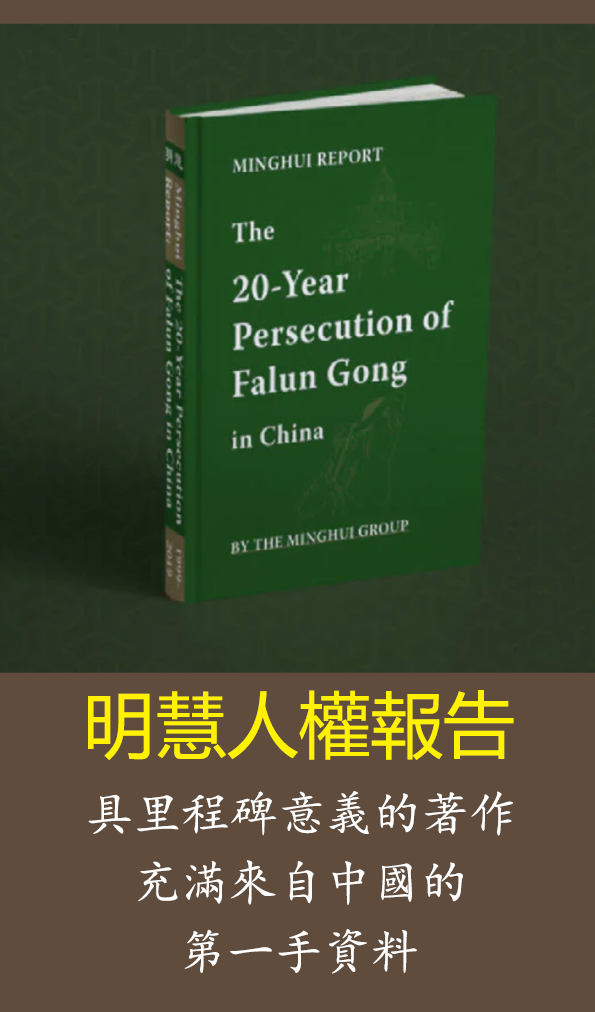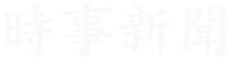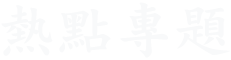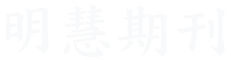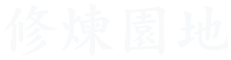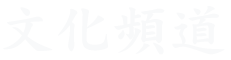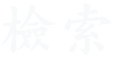寧夏婦女李金花自述遭迫害經歷
我叫李金花,今年四十三歲。我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修煉法輪功以前,我的體質非常差,稍不留心就感冒、發燒,肺炎就犯了,吃藥打針幾乎沒有斷過,每月來例假血多、持續時間長,渾身無力,幹不了重活,幹活幹一會就累,就要休息。結婚後因為帶孩子辛苦,身體就更虛弱。一九九五年嚴重貧血、經常頭暈目眩、血色素低,到醫院檢查後醫生當即要求住院治療。我相繼住院兩次,每次住院近兩個月,醫藥費花去了近萬元。最後醫生抽我的骨髓也未能查出病因,無奈之下只有出院。出院後又吃了很多補藥也未見效果。那時見我的人說我臉色蒼白。因身體不好,脾氣也不好,每天悲嘆自己命運多慘,幻想著誰能幫我減輕痛苦。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和家裏其他四人同時開始修煉法輪功,短短幾個月後我們幾個人的身體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再不感冒了;每次來例假正常了;臉色漸漸紅潤,體力增強了;因為身體好了,對別人能寬容了,心胸開闊了,精神面貌徹底改變了。幾個月後家人不放心,非讓我到醫院檢查,結果一切正常。我母親有甲肝、胃下垂、腹腔裏還有個腫瘤,中西藥沒斷過,是個「藥罐子」,從我記事開始,我家每天都瀰漫著熬中藥的苦味,但從得法至今再沒吃過一片藥。我父親有嚴重的胃病,修煉後也都好了。我女兒雖然小,也受益無窮。
我們修煉後,都努力按法輪功師父的教導「真、善、忍」的標準做人,在生活、工作中無私無我、先他後我;和別人發生矛盾都能夠找自己的不足。我們沉浸在修煉法輪功後的喜悅中,只要有時間就到煉功點煉功。當時我所在的銀川火車站門口的煉功點每天都有一百多人,再後來因為人多就分成了幾個點。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澤民集團利用國家機器迫害法輪功,一時間電視、報紙大面積污衊法輪功和大法師父,警察到處抓人。不久我們煉功點的輔導員王玉周被綁架了,同修馬智武(至今仍在監獄)等都被勞教了。新聞媒體黑白顛倒、編造謊言欺騙世人;警察四處抓人,肆意製造恐怖氣氛。我們不明白為甚麼會發生這種事情,這麼好的功法不讓煉了,難道做個好人有錯嗎?我開始向身邊的人講述煉功後身心受益的情況。我想:既然不讓煉,肯定是政府不了解法輪功。我在醫院花了那麼多錢都沒治好的病,花了十二元錢,請了一本《轉法輪》(法輪功的主要著作),煉功短短幾個月就好了,我怎能讓人誣蔑師父呢?我一定要為師父喊冤!
在本地上訪無門的情況下,二零零零年二月底,我帶女兒(六歲)同哥哥李世林去北京上訪。可是從那以後我卻被多次抄家、綁架、勞教、判刑,至今家散人離、居無定所、一無所有、幾次丟掉工作……我哥哥李世林也被非法勞教、判刑、多次綁架抄家。
我的經歷可以讓世人知道中共邪黨是如何迫害人的正信、怎樣迫害一個手無寸鐵的善良民眾的。以下是我和家人十二年多來所遭受迫害的簡述。
1、合法上訪被綁架
二零零零年二月底,我和女兒、哥哥李世林一同去北京上訪。那時公安部門已在全國的飛機、鐵路、公路上設置關卡,檢查、阻止法輪功學員到北京。我們去北京的途中在火車上就聽說寧夏同修司玉蓉、陳玉蘭等五人在火車上被綁架了,但我們還是沒有退縮。到北京後,只見漫天黑雲滾滾,到處鬼影幢幢。幾天後我們三人到天安門廣場,又碰上了寧夏大法弟子王玉柱(至今還在監獄)、秦永順。我看見天安門廣場上、廣場周圍停了好多輛警車,到處可見警察、便衣在抓人打人,只要發現法輪功學員就直接抓走,根本沒有申辯的機會。
當時王玉柱、秦永順拿出一個長長的條幅剛打開了一半,周圍就撲過去七八個警察搶條幅、打人。警察把他倆按倒在地、不分輕重不停的拳打腳踢。一個警察還用腳狠狠地踩住秦叔的頭,秦叔不停的高喊「法輪大法好」,警察見狀打的更厲害了,後來又把他拉起來打耳光。當時圍觀的人很多,但這些警察絲毫沒有收斂。
惡警雖然殘暴,我們還是毅然把寫有「法輪大法好」的橫幅打開了。瞬間衝過來好多警察、「便衣」把我們團團圍住,他們把我哥按倒在地,拳打腳踢。我女兒看到這恐怖的一幕嚇呆了,站在那兒一動不動。
隨後我們五人都被綁架到一輛警車上,當時那輛車裏已經有十幾個大法弟子了,警車裝滿大法弟子後呼嘯著將我們押到廣場東側的派出所。
2、天安門廣場東側派出所警察的惡行
廣場東側的派出所有一個特製的巨大的鐵籠子,我們去的時候裏面已經關了好多人了。周圍有警察值班,值班警察隔著鐵籠子問我女兒:你還煉不煉?我女兒天真無邪的看著他,笑嘻嘻地回答:「煉。」那警察惡狠狠地說:你再煉,再煉我就讓你夭折了!所謂人民警察在一個幼兒眼中儼然是一個惡魔。
鐵籠子旁邊的辦公室不斷有警察出來將大法弟子逐個帶到辦公室,逼迫說出姓名和所在地,不說的又帶回來了。秦永順被帶走大約兩小時才回來。警察帶他返回鐵籠子時,他的兩條胳膊都在發抖。我問他胳膊咋了,他說被電棍電的麻木,已經不能控制了。和秦叔同去的同修說秦叔在裏面被惡警電了好長時間。後來我哥也被帶走了。
過了一陣,我也被警察帶到這個挺大的房子裏,我看到幾處多個警察圍著一個大法弟子施暴的場景:一進門地上躺著一個小伙子,已經失去知覺了(後來知道是河南的),一個警察穿著皮鞋狠狠的踩在他的臉上,他女朋友被打著「背銬」站在旁邊,惡警不讓她靠近。她女朋友哭喊著說:人已經昏迷了,你們還打?幾個警察圍著一個東北的女大法弟子,正在逼問她,她的眼睛和嘴都被打腫了,眼圈周圍青紫,嘴角正在往下流血;一位頭髮全白精神矍鑠的老太太被幾個警察圍著逼迫她蹲馬步,她還是不肯說姓名。三個警察正在強行給我哥打「背銬」:他們把我哥按著趴在桌子上,一個又高又壯的警察用膝蓋頂在我哥的腰上,三人使勁將我哥的兩條胳膊往手銬裏銬,只聽骨頭嘎嘎作響。強行給我哥銬上後,他們又反覆逼問姓名和所在地……
帶我的警察故意走得很慢,讓我看這些血腥場面,目的是嚇唬我。這些殘忍的場面以前只在電視劇裏看見過。怎麼能這樣對待做好人的人呢?我氣得渾身發抖。他們開始問我姓名、所在地,我也不回答。兩個警察把我的胳膊一條從前面繞過肩頭往後往下拉,一條從背後順著脊背往上拉,我奮力掙扎,也無濟於事。他們強行給我打上「背銬」的一瞬間,我疼的像要死了。我的左胳膊小時候摔斷過,這樣銬著,我真感覺生不如死,大約十幾分鐘我受不了了,就說出了姓名。後來聽說王玉柱那天也被打的很厲害。我們所有人當天被綁架後都沒吃沒喝。晚上九點多我們寧夏大法弟子全被帶到寧夏駐京辦了。
3、被非法關押在銀川市看守所
我們到寧夏駐京辦,那裏非法關了近百個寧夏大法弟子。當時駐京辦已經去了好幾個寧夏公安部門的警察。大法弟子男女分開關在兩個大房子裏,門口有警察把守。警察偽善的對我們說:沒事,你們回去就可以回家了。第二天,一百多人一起坐火車被押送至銀川。到銀川火車站一出站,門口就有好多輛警車排了兩排,警察指揮著大法弟子上了提前安排好的警車上。我和馮建英、張桂芳、張芳、郭文燕、秦永順等十幾個大法弟子被押到銀川新城(現改為金鳳區)分局。警察通知我丈夫到新城分局接孩子時,警察問他:你知不知道你妻子走北京?我丈夫說:我和她早都沒關係了,他氣狠狠的把女兒接走,沒有理我。隨後我們被押往銀川看守所。
當時關押在看守所的女大法弟子有三十多個。看守所就是人間地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裏面只有一個通鋪,十幾個人都睡在大通鋪上,人多時大家都只能側身睡覺,根本沒有翻身的餘地;晚上輪流值班,吃喝拉撒全在這一間小房子裏,如果有人吃飯就不能上廁所,即使肚子不舒服也得忍著;剛進去的時候還要被號長打;每天必須洗廁所、擦地;吃的飯跟豬食差不多:黃饅頭和土豆湯,土豆湯都磣牙。
我們去的當晚在號子裏煉功,被人誣告了。第二天,隊長馬愛玲把我們十幾個煉功的人叫到辦公室,讓大家站成一排。她氣急敗壞的拿著一本書把所有人逐個從臉上扇,邊扇邊罵:你們跑這來煉功!後來她問我還煉不煉?我說煉!馬愛玲就又叫來其他隊長合夥給我打了背銬、戴上重刑犯戴的腳鐐。時間不長,我的胳膊青紫淤血,好像要斷了,她們就給我卸掉了。馮建英不配合邪惡,被戴上重刑腳鐐、打背銬十三天。
我被戴腳鐐、打「背銬」、遭惡警辱罵,加之吃不好睡不好,身體扛不住,出現流鼻涕、咳嗽、高燒不退、渾身無力的症狀,十三天後回家了。回家不久,得知我哥、王玉柱、馮建英、趙玉虎(至今還在監獄)等同修都被勞教了,有的大法弟子被勒索了一筆錢回家了。
4、家散人離 孤身回娘家 女兒受折磨
九九年上半年,我丈夫就有了外遇,提出離婚,我不同意。我是一個傳統的女人,把家看得很重,他的家人也都指責他,不同意我們離婚。後來我丈夫就住在那女人父母留下的房子裏不回家了,而且不給家裏錢,還用種種手段找茬欺負我。九九年七二零之後,邪黨的媒體大肆誣蔑法輪功,我丈夫竟然給他家人說:因為她煉法輪功要和她離婚!他年近八十的老父親聽說後,吃力的上到我家住的五樓,勸我不要煉法輪功了。我就給老公公解釋說,他兒子要離婚是因為有外遇,不是因為我煉法輪功。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上訪被關押從看守所回家後,我丈夫再次以我煉法輪功為藉口,提出離婚,我還是不同意,他就起訴到新城區法院。起訴書上寫的是:因我煉法輪功,到北京「靜坐鬧事」,給他「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並且執意要女兒和房子,我還是堅決不離。法院送來傳票,我無奈之下到法院應訴。我們家所有財產折算了四萬塊錢左右,誰要房子就給對方兩萬塊錢。我丈夫提出:如果我要房子必須馬上給他兩萬塊錢。我當時拿不出錢,考慮再三,答應將房子給丈夫,但女兒我堅決不同意給他。我丈夫說:我怕女兒跟上你煉法輪功!新城區法院(現改為金鳳區法院)的法官翟淑君(女)、書記員鄧麗(女)在裁定時對我說:孩子六歲多,母親照顧最好,但是因你煉法輪功,就只能判給你丈夫,還說:你不同意我們也可以這樣裁決,只不過時間長一點。
那時我已經失業、丈夫長期不回家、不給我和女兒生活費、偶爾回來一次還找茬鬧事。又拖了一段時間,我見沒有轉機只得簽字。女兒得知我們離婚,她和媽媽要分開時,哭的死去活來。法院調解時丈夫答應給我的兩萬塊錢兩年多才陸續給清。
沒有工作、沒有住處、女兒被搶走,加之受迫害身體不好,我萬念俱焚,一無所有,孤身回到父母家。
從那以後,我丈夫及他家人害怕女兒跟我煉功就不讓我們見面。我大多只能到女兒的學校偷偷見她。女兒一方面因想念媽媽而痛苦,另一方面又因見我遭毆打、謾罵,還要接受一個後媽的管教,她的痛苦可想而知。一次女兒得到允許到我父母家住了兩天回去後,被她爸爸搧耳光,把門牙打掉了一塊;她爸爸、奶奶、姑姑還用掃帚把打她的腿和屁股,她好長時間走路一瘸一拐。此後我起訴到法院,惡黨法官再次剝奪了我要回女兒的權利。後來有一次因女兒偷偷跑來見我,被她奶奶知道後趕出家門,才和我生活在一起了。但她爸爸在之後的兩年多裏不給她生活費。直到二零一零年上高二時,需要在學校附近租房,我一人實在無力承擔,女兒去找他爸爸要,才又開始給。
5、被非法勞教三年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和申冬梅散發真相資料時被惡人構陷,遭滿春鄉派出所的惡警綁架。派出所惡警逼問申冬梅(二十二歲的姑娘)姓名時,她不說,惡警打了她好幾個耳光,把她的衣服扣子都撕掉了。我們在派出所呆了一陣,銀川市公安局的李存、譚江萍等人到派出所非法審問我們,李存同時派了十幾輛警車到我父母家抄家搶劫,還威脅恐嚇我七十多歲的父母。我父母經歷過多次的「運動」,非常害怕,就把打印機交出來了。當天晚上我們被送到銀川市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他們迫使我們當「奴工」撕膠,每天都有很重的任務,幹不完不讓睡覺。一個多月後我倆被非法勞教三年,同時關押到寧夏女子勞教所。
在勞教所,每個法輪功學員都有兩個「包夾」看管,無論白天晚上都跟在身邊寸步不離的監視;警察每天還給我們放污衊師父的錄像、寫思想彙報;「坐小板凳」;撿脫水菜,任務很重,幹不完不許睡覺;還到南梁農場挖葡萄溝、剪樹苗。中隊隊長馬曉燕、警察馬莉經常找我談話,讓我放棄修煉,還偽善地勸我「轉化」,不「轉化」就不讓家人接見。有一次,我爸爸和女兒來看我,她們不讓見。我女兒在接見室嚎啕大哭,我父親哭著給他們說好話,警察才讓接見了。
在勞教所,警察和警察指使的犯人每天花樣繁多的迫害手段和幹奴工讓我心力交瘁、度日如年,加上長期學不上法、人心重,就違心地寫了「三書」,提前回家了。這次寫「三書」給大法抹了黑,對不起師父,也加大了自己以後修煉道路上的魔難。
6、再次被綁架關押在看守所
我和我哥相繼從勞教所回家後,滿春鄉派出所和城區公安分局(現改為興慶區公安分局)的惡警經常到家騷擾,為避免父母受迫害,我和我哥就租房搬出去了。
就在我們回家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二零零二年一月,銀川市公安局的譚江萍等惡警為了他們能「過好年」,就到我父母家找我們。我倆不在,他們把我七十歲的老父親綁架到滿春鄉派出所關了一夜。我們聽到消息第二天回家後,李存、靳春花、譚江萍,張安忠等惡警當即把我倆綁架上了警車,欺騙我們說是到銀川市公安局,實際上警車直接開到了銀川市看守所。李存、張安忠等到看守所提審我時,我質問他們為甚麼騙人,他們說:「不騙你們,你們怎麼能來呢。」
這樣我又被非法關押了兩個多月,我哥被非法關押一個多月。
7、我和哥哥李世林、朱琳一同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三年六月的一天晚上,十二點了,我和朱琳在租的房裏,正準備睡覺。突然聽到有人在開門,我以為我哥來了,打開門一看是李存一夥。他們押著我哥,從我哥身上搶了鑰匙正在開門。我哥的一條胳膊打著繃帶,吊在脖子上(後來才知道惡警綁架我哥後用吊銬吊了三天三夜,胳膊快斷了,我哥承受不住說了我們的住處)。惡警見我們打開了門,立刻衝進來,將我們三人戴上手銬綁架到一個隱秘的地方,分開關押。
第二天上午,張頂生帶人開了兩輛車押著我到我和朱琳租住的房子搶劫了大法書、打印機、真相資料、一些私人物品、兩千元現金;到我哥租住的房子搶劫了大法書和一些私人物品。當晚,我乘機從關押我的地方跑到大街上攔了出租車準備離開,靳春花、馬自立在後面追趕,路過的行人抓住我後交給靳春花、馬自立。回到原地,靳春花氣呼呼的搧了我一耳光,還慫恿張頂生繼續打我。張頂生把我銬在暖氣管上好長時間,我的手腕勒出了深深的一道血印子。當晚就把我關押到銀川看守所了。
過了幾天我哥和朱琳被關到「六一零」洗腦班,再後來也關到看守所了。到看守所我絕食抗議,七天水米未進。隊長張芳和所長揚言要給我灌食。我想:有的同修因灌食被迫害致死了,我還有年邁的父母、可憐的女兒沒人照顧,就放棄了。後來又絕食兩次,都沒有堅持太久。因我幾次絕食瘦的皮包骨頭、弱不禁風。
三個多月後,銀川市興慶區法院的法官、興慶區檢察院的檢察官給我、我哥、朱琳分別判刑三年、四年、三年半。我們三人被非法開庭時,沒給家人通知、不讓辯護,開庭時間不長就草草結束了。我們上訴到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中級法院給我們送來《刑事裁定書》稱: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中級法院參與迫害的是:審判長:周寧林;代理審判員:馬少駿、李鋒;書記員:劉春豔。十幾天後我們就被關押到監獄了。
8、在寧夏女子監獄遭受的迫害
我和朱琳同時被關到了寧夏女子監獄。剛去,我們的頭髮就被強行剪成短髮,有不願意剪的,幾個惡警上去按著就強行給剪了。在這個黑窩,法輪功學員仍然是被重點監控的對像,每個人都有兩名「互監」全天二十四小時負責監視,一言一行都沒有自由,上廁所「互監」也跟著。每頓飯吃飯的時間很緊,吃飯慢了,獄警、「互監」就罵罵咧咧。
惡警安排監視我的「互監」是兩個殺人犯,一個叫宋淑萍。從早到晚看管我,就連我半夜上廁所他們都跟著,寒冬臘月也不例外。我們每天只能幹活、吃飯、睡覺,不允許提法輪功的話題。
我被分配幹奴工燙衣服。在車間幹活時「互監」還監視著,不讓說話;飯前飯後還要訓隊列、背監規、唱邪歌。有一次開會時,法輪功學員席華不配合邪惡,中隊長陸春、小隊長楚楠等和一幫犯人一哄而上連拉帶扯強行給席華戴上手銬拉走了。教育科的丁蕾、還有陸春、三隊隊長方梅經常找我談話,讓我「轉化」,並每天逼我寫思想彙報。
法輪功學員不「轉化」的,就不讓接見;不讓家人送東西,只讓壓錢;裏面賣的東西都是天價劣質的;不讓打電話;不讓通信。中共惡徒一方面不讓法輪功學員與家人見面、通信、打電話,一方面還在媒體造謠說法輪功學員「不講親情」。
靈武大法弟子駝美玲,被他們折磨的精神恍惚,神智不清,聽犯人說,有人給她的食物裏放了不明藥物。在這種高壓迫害下,自己法理不清、人心太重,再次「轉化」,提前一年回家了。回來後經過學法,對自己的行為痛悔不已。我辜負了師父的慈悲苦度,再次給大法抹了黑。
9、再次無辜被綁架關押到看守所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中午,我正在租的房子做飯,突然有人敲門。幾分鐘後我想出去看看究竟誰在敲門,剛下到一樓就有人喊我。我一看是個不認識的人,他周圍還有一夥人,其中有兩個穿警服的。我走近一看這夥人中有一個是銀川市「六一零」的王滿。這時過來一人(後來知道他叫駱健)說:我們要抄你家!我堅決不配合。
正在這時,我女兒放學回來了,我把身上的零花錢給她,讓她去奶奶家吃飯,女兒拿了錢就走,走了不遠,王滿追過去,抓住我女兒的手腕把我給的零花錢一把搶過去,將上面寫有「法輪大法好」的幾張搶走。還把我女兒的手腕上捏出一道紫印子。
駱健逼迫我開門,我據理力爭:「我只是煉法輪功做好人,又沒犯法,你們這樣三番五次的無故騷擾、迫害我,我在這租房子帶著孩子上學,你們憑甚麼?」駱健見我不開門,就給開鎖的人打電話。打完後又把我往樓上拽,最後強行從我兜裏搶走鑰匙打開門。這一幫人,擠進三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開始搶劫,翻箱倒櫃抄出大法書、電子書、《明慧週刊》等。
非法搜了一番後,駱健又打電話叫來幾個人,一個進屋後拿著攝像機亂拍亂照,另外的幾個又到處亂翻了一通,包括陽台。駱健指使這些人綁架我,我坐在門口抓著門死死不放。駱健又打電話叫來防暴大隊四個當兵的。這四人來了強行給我打上背銬,將我抬到車上,綁架到西夏區公安分局,銬在鐵椅子上。
 酷刑演示:鐵椅子 |
後來得知參與綁架我的是寧夏公安廳的駱健、銀川市「六一零」的王世元、王滿,西夏分局國保大隊的陳建華、李蘭,西花園派出所所長張中、西花園居委會主任王紅梅等。
當天下午,王世元、陳建華等將我綁架到看守所,我堅決不下車,他們把我強行拉下車,推到看守所。我看到大法弟子辛林原也被綁架到這了。獄警不讓我穿涼鞋,將我光著腳押到二樓監區的號子裏。剛到號子裏,獄警就指使吸毒犯張學萍對我搜身。搜身後,張學萍命令我坐到床上,我坐下後習慣性的盤上了腿,她衝過來打了我兩個耳光。我報告給隊長張某某,張某某佯裝不知,還叫過吸毒犯小聲嘀咕,讓對我嚴加看管。張學萍還逼迫我每天洗廁所、擦地。
我不是罪犯,就不吃飯不喝水。三天後,姓張的隊長恐嚇我:你不吃飯,我們就給你強行灌食,這裏關押過的法輪功絕食的多了,誰也沒抗住,你還是吃吧!所長惡狠狠地說:這裏關了多少人,我還管不了你了?你趕緊吃飯!張隊長又指使號子其他人圍攻我,我不吃飯她們就不停的辱罵師父。有一個叫吳小丹的魔性大發,不停的污衊大法、辱罵師父,其他人還誇獎吳小丹。我萬分難過,為了不讓她們再造業,就進食了。
我還沒有完全恢復體力,獄警就強迫幹奴工了。裝打火機,每人每天分一臉盆,新來的減半;每天從早上六點多就開始,一直幹到晚上,幹不完就不讓睡覺;幹了十幾天後,我的大拇指、食指的皮就磨爛了;因為長時間坐在小凳子上,屁股磨的疼痛難忍,有些人就想辦法用舊衣服等改成小墊子墊上;每頓吃饅頭,喝蓮花菜湯;每天早晨唱邪歌、晚上看「殃視」新聞、背監規;我堅決不穿號服,犯人在隊長的指使下,每次都一擁而上強行給我套上。有個叫馬玉鳳的獄警特別邪惡,只要輪到她點名就用髒話侮罵我,還罵我是另類,讓其他人對我嚴加看管。
在這期間,駱健、王世元、王滿、陳建華多次輪番到看守所非法提審我和辛林原。有一次,王世元提審時我甚麼也不說,王世元惱羞成怒,端起一杯水潑到我臉上。一次駱健提審時威脅我:從你家搜出的傳單數量不夠勞教,我可以說你是屢教不改,照樣可以勞教你三年。最後一次,王滿、陳建華拿出寫好的一張紙,裏面有不發傳單、不上網、不和其他大法弟子接觸、別人給東西不要等內容,逼迫我簽字,我這次被非法關押了二十六天。
此次我被非法關押期間,我八十歲的父親、七十六歲的母親、女兒、哥哥等親友前去要人,他們不但不放人,還非法拘留了同修隆竹雲、蹲坑抓我哥、到其他同修家騷擾。遭受此次打擊後,我父母的頭髮一夜之間幾乎全白了。
10、家人遭受的迫害
(1)女兒遭受的折磨
二零零零年我被綁架關押回家後,法院協同丈夫逼迫我離婚。我丈夫雖然執意要去了女兒,但他對女兒並沒有盡到當父親的責任。女兒有時在爺爺奶奶家住,有時她爸爸帶回去住。孩子的爺爺、奶奶、爸爸、姑姑聽信了邪黨的謊言,生怕女兒跟上我學法輪功,就不讓我和女兒見面。我只能隔三差五到學校偷偷和女兒見上一面。每次見面時女兒都哭著說:媽媽我想你,我在奶奶家不敢哭,我一哭爸爸、奶奶、姑姑都罵我,我只能躲在被窩裏哭。女兒和我見面,一旦被她爸爸家的人知道就大聲斥責、謾罵。
有一次週末我徵得她奶奶同意後將她接到我母親家住了兩夜。我送她回去時,她爸爸、奶奶、姑姑都在,她爸爸將我衣領扯住想要打我,我制止後,他將我推出門,關上屋門就開始打女兒。我站在門口聽見女兒哭的撕心裂肺,使勁敲門,她們都不開,我只能傷心的哭著離開了。第二天,我到校門口,遠遠看見女兒一瘸一拐的走出來。女兒一看見我抱住就哭。我問咋了,女兒哭著說:他們怕我去姥姥家煉法輪功,爸爸搧我耳光,把我的門牙打掉了一塊;還說要把我的腿打斷,邊打還邊問:你還煉不煉?後來爸爸、奶奶、姑姑都用掃帚把打我的腿和屁股。我看到女兒的一顆門牙被打掉了一塊、大腿上一個硬疙瘩,隔著褲子都能摸出來。我和女兒站在學校門口擁抱著哭了好久才分開。
此事過後,我起訴到法院,要求自己帶女兒,而且我女兒已十四歲,可以自己做主選擇了。金鳳區法院的法官王振華無視我和我女兒的請求,再次以我煉法輪功不適合帶女兒為由,剝奪了我要回女兒的權利。
我離婚女兒被判給她爸爸七年多後的一天,女兒又跑來見我,被她奶奶知道了趕出家門,才終於和我生活在一起了。雖然女兒回到我身邊了,但他爸爸在此後的兩年多裏沒給過一分錢的生活費。女兒上高二後,因需在學校附近租房,我一個人實在無力承擔,女兒找他爸去要,他爸才又開始給生活費了。
我女兒從六歲至今,十二年裏經歷了一個孩子不該經歷的魔難,承受了一個孩子不能承受的痛苦。我的公公、婆婆、小姑子都是善良的人,如果不是邪黨的謊言欺騙,他們絕對不會如此對待我和女兒的。邪黨歷次搞運動整人時,都要讓家人和所謂的「罪犯」劃清界線。歷次運動中父子反目、夫妻成仇、手足相殘的例子比比皆是。邪黨迫害法輪功的謊言毒害了無數無辜的世人,讓他們現在承受壓力,將來還要償還褻瀆佛法而造下的天大罪業,而這才是最可怕的。
(2)父母遭受的迫害
我父母因我和我哥的多次被關押在看守所、勞教所、監獄,警察多次到家中抄家騷擾,他們受盡魔難,整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和同修申冬梅被綁架後,滿春鄉派出所的警察三天兩頭到家裏騷擾,而且大多是晚上去。有時我父母剛睡下就有人咚咚砸門,嚇的他們徹夜不眠。二零零二年一月,銀川市公安局的譚江萍等惡警為了誘捕我和我哥哥,將我七十歲的老父親綁架到滿春鄉派出所關了一夜。二零零三年我和我哥同時被判刑,他們痛苦的都活不下去了。以至後來我父親只要見警察來家裏,又驚又氣,頭就開始劇烈疼痛,躺在床上就起不來了。我和哥哥遭受迫害時,兩位老人不得不拖著沉重老邁的步子到處要人、奔波,經常遭到惡警的冷眼和辱罵。二零一一年八月我被綁架關押回家之後,春潤園居委會的人還幾次到家裏騷擾,逼迫他們簽字。
從邪黨迫害法輪功至今的十二年中,銀川市「六一零」警察、滿春鄉派出所警察、春潤園居委會工作人員到我父母家騷擾抄家就像家常便飯。我父母承受的壓力和痛苦一言難盡!
(3)哥哥李世林遭受的迫害
我哥哥李世林二零零零年二月底到北京上訪,被綁架後,遭勞教迫害一年。二零零二年一月,銀川市公安局的譚江萍等惡警為了他們能「過好年」,到我父母家找我和我哥。我倆不在,他們把我七十歲的父親綁架到滿春鄉派出所關押了一夜。我們聽到消息第二天回家後,李存、靳春花、譚江萍,張安忠等惡警將我倆綁架。我被關押了兩個多月,我哥被關押一個多月。二零零三年六月,我哥哥、我、朱琳一起被綁架同時被判刑,我哥四年、我三年、朱琳三年半。
二零零七年八月,我哥陪同大法弟子馬智武的親友到吳忠監獄看望馬智武,吳忠監獄教育科尹自能叫來吳忠國保大隊的惡警,將他們一行綁架到吳忠高閘派出所,關押了一夜,每人還勒索了二十元錢。惡警綁架他們時施暴,我哥回家後胳膊青紫。
在中共迫害法輪功至今的十二年多裏,我屢遭迫害,幾次走投無路。因為信仰支撐著我、師父呵護著我、父母關心著我、同修鼓勵著我,雖然修煉的路走的磕磕絆絆,我還是堅強的走到了今天。因承受不了迫害,違心被「轉化」是我修煉路上的污點,是修煉人的恥辱。在此,我嚴正聲明:所有在高壓迫害中不符合大法要求的言行一律作廢!
我從小體弱多病,本來是一個不幸的人,萬幸的是我遇到了法輪大法。雖然中共迫害法輪功以後我和家人遭受了許多魔難,但我矢志不移。唯願世人明白真相,擁有未來!包括那些曾經參與迫害過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