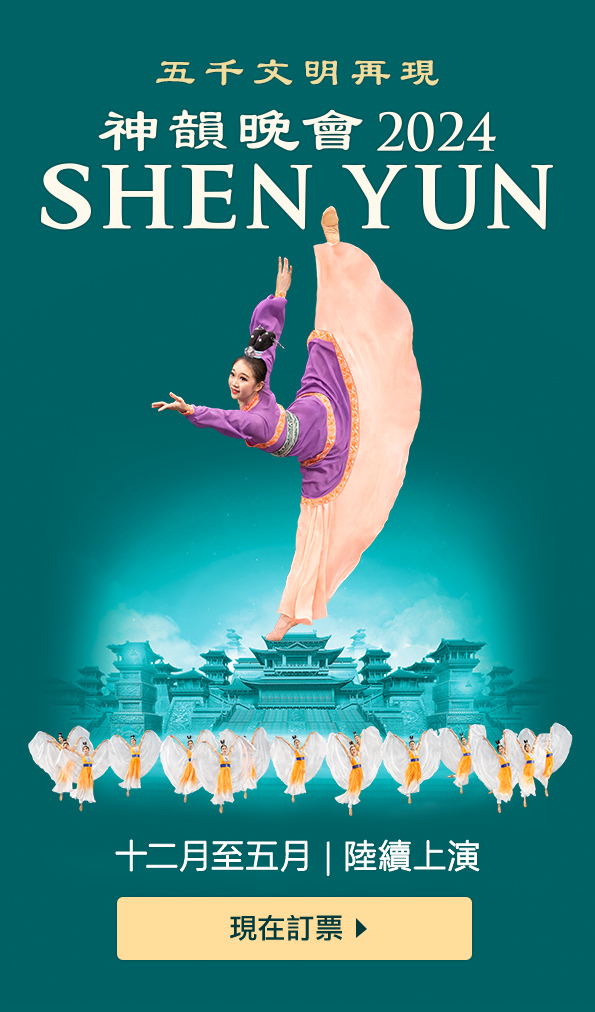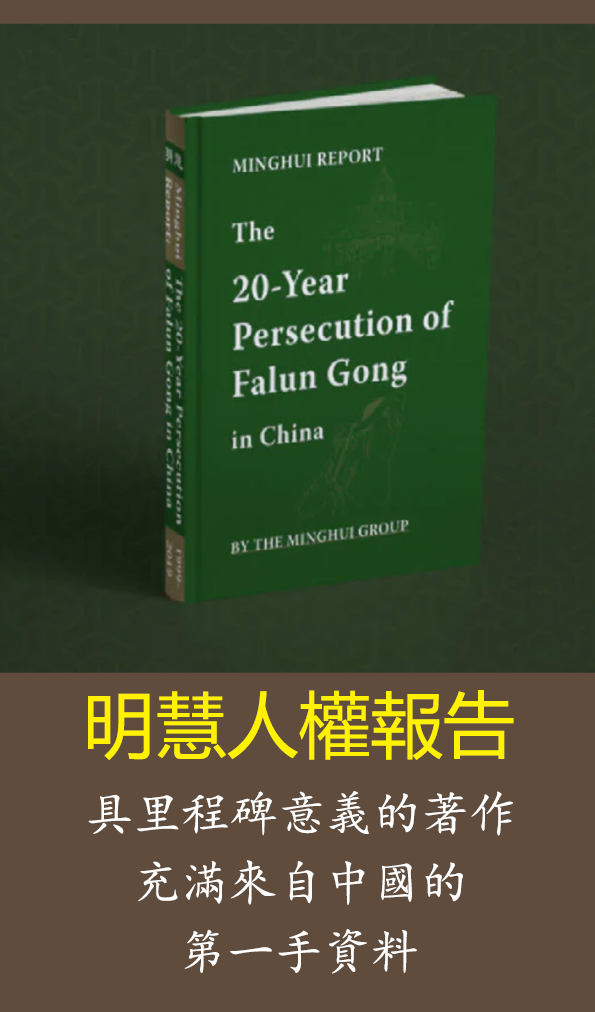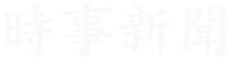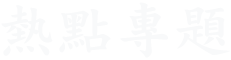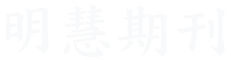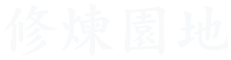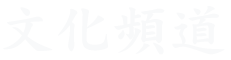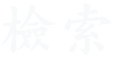美麗灘塗上的罪惡
1、被誣陷遭迫害
那是二零零零年的十二月十二日,也是我被當地610綁架到當地看守所,非法關押的第366天,早晨六點多鐘,邪黨當地法院的人和當地公安分局的人就開始唱雙簧了。早在二零零零年的六月十六日,他們秘密開庭,違法審理,起訴誣陷我的所謂罪名是「破壞國家法律實施」。我拒絕法院給指派律師,為自己作了無罪辯護。因為我只是按「真、善、忍」做一個好人,並沒有破壞任何一條法律的實施。其實判決在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就下來了,為甚麼拖到二零零零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宣判?先是法院的人宣判不追究刑事責任,然後公安分局的人宣布勞教兩年,迫害的誣陷藉口也由「破壞國家法律實施」改成了風馬牛不相及的「擾亂社會秩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作為法院、公安的國家公務員,拿著人民給的優厚俸祿,本應伸張正義、維護善良,然而,他們卻狼狽為奸,加害我這個遵循「真、善、忍」 的普通百姓。這就是邪黨披著「為人民服務」的外衣,幹盡殘害善良民眾的醜惡嘴臉。難怪時下流傳著:只有你想不到的罪惡,沒有××黨幹不出來的罪惡。就這樣,在當地區公安分局前副局長×××和610暗箱操作下,當天我和另外三個大法弟子,被綁架到惡貫滿盈的江蘇省方強勞教所迫害。
2、結識同修奚旭東
剛到黑窩的入所隊,我認識了一個常州的大法弟子,已退休的高級數學教師、六十八歲的奚旭東。老人是因為在北京天安門金水橋上,高舉「法輪大法好」橫幅而遭迫害的。老人話不多,然而在他那白皙而又清瘦的面容上,平和中透著堅毅。我時常被他為真理捨死忘生,而感動的流淚。邪黨怎就一個「邪」字了得?竟把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也要勞教迫害。十餘天後,我被分到一大隊迫害。
3、揭「天安門自焚」謊言
二零零一年一月下旬的一個晚上,警察突然召集看電視,內容竟是「天安門自焚」偽案。邪黨連遮羞布也不要了。我就用觀後感的形式,逐一揭露了中央電視台卑鄙造假的行徑:天安門廣場是世界最大的廣場,廣場內沒有可燃物,瞬間從哪兒冒出那麼多滅火器?每逢節假日,天安門廣場人流如潮,為甚麼新年除夕的下午,廣場上除了警察就是自焚者?所謂學法輪功七八年的老學員「王進東」,腿還翹很高,且成「V」形的散盤?大法弟子們表達的心聲是: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師父清白!而「王進東」喊的話不倫不類。那「王進東」表演的分明不是法輪功學員,倒恰似邪黨慣用套路虛假的英雄人物。電視裏聲聲稱是突發事件,但鏡頭拍的卻很全,有遠景、近景、還有特寫。邪黨的廣場監控器也邪乎,它能跟蹤拍攝,這也是邪黨的特色?河南開封只是個一般的城市,普通話普及的還真好,上場表演自焚者無論老幼,張口閉口都是很地道帶京腔的普通話。北京積水潭醫院更讓人拍案叫絕,竟從埃及古墓學了一招,用「木乃伊」包紮法治療燒傷患者。林林總總,漏洞百出。
4、奴工迫害
一大隊離所部最近,是黑窩樹的邪惡先進典型,搞造型、作秀、造假是它的拿手戲,以教導員王飛為首的一夥惡警,自然就成了惡黨迫害大法弟子的馬前卒了。我到一大隊正是隆冬,不久就開始挖河工。天不亮就起床出工,凜冽的寒風呼嘯著,月亮還懸在空中,銀白的月光洒在空曠的田野上,又平添了幾分瑟瑟寒意。寂靜的曠野中,有一種不知名的鳥在淒楚的叫著,那些勞教聽出的鳥叫聲是:方強好苦,方強好苦。工地離一大隊監區要走三十來分鐘的路程,就這樣又一天的奴工開始了。細心的親人,雖然早已給我備了一雙雨靴,然而雨靴很快就被蘆葦茬扎破了,淤泥灌進雨靴裏又冷又滑,只好光著腳踩著兩公分厚的冰抬河泥,蘆葦茬扎破腳是常有的事。
一大隊分大田組和縫紉組兩部份。南京一位五十九歲的大法弟子劉伍堂,一直在縫紉組,開始挖河卻把他安排到了大田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們想用超強奴役來摧垮大法弟子的意志。
大概在四五月份的時候,我四弟和我的同學,帶著我女兒去探望我。中午,他們在一大隊監區的大門口等候張望,當我們收工快到大門時,我所在的那行隊,也就是僅有的十幾個人,他們已經搜尋了好幾遍也沒找到我,我被迫害的連親人都辨認不出來了。當我給他們打招呼時,他們才認出了我,頓時他們三人全都哭了。
六月份往稻田裏施肥,每人要扛一袋一百斤重的化肥,遠的要扛著化肥走700多米,而且是在又窄又滑的田埂上走,稍不注意就會連人帶肥一起摔進水田裏。這時帶工警察的「快快快」聲響起,初來乍到的還以為真的是人性化管理呢,緊接著就是警察的呵斥謾罵聲。警察關心的是化肥潮沒潮,至於人是否摔傷「人民警察」睬也不睬,他們只把人當作奴役的工具。稻田水深行走困難,一手把持裝化肥的盆,一手撒著肥,撒的又要快,還要撒的勻。由於機械的、不停的撒,抓肥那隻手的小指外側都磨出了血泡。烈日炎炎,稻田裏的水都曬的發燙。火辣辣的太陽,彷彿要透過被汗水浸濕的衣衫,把人的肌膚烤焦。帶去的自來水早已喝完了,臉上大汗淋漓,而嘴裏發乾、發澀,口渴難耐,沒辦法,我只有俯身喝溝渠裏的水解渴。一天下來,精疲力竭。邪黨是從來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
5、生活上迫害
我在黑窩的一年時間裏,曾在一大隊、三大隊、七大隊遭迫害。一大隊的伙食和其他大隊的伙食一樣糟糕,雖然每天幹十幾個小時繁重的體力活,連最起碼的飯都吃不飽。早上是一個一兩多的小饅頭、一碗前一天晚上吃剩的米飯燒成的稀飯,七八天才可能有一次鹹菜,就這點飯食要支撐五六個小時的重體力勞作;有的勞教嘲諷的說,中午、晚上都是九菜一湯。理解成「九」那可是自作多情了,其實就是韭菜湯,外加一圓鋁盒永遠都吃不飽的陳年米飯。當質問警察伙食為何這麼差時,回答一般有兩個版本。第一個虛偽版本:政府撥的錢太少。而警察吃的伙食,卻是剋扣被關押人的伙食費和每人每月的勞教金。第二個變態版本:這又不是療養院,伙食好又吃的飽,下崗工人都要往這跑。家裏能給送錢的就買火腿腸和方便麵來充飢,沒錢的就只有挨餓了。
在七大隊遭迫害的兩三個月的時間裏,幾乎就沒吃過熟饅頭,饅頭半生不熟的,還發粘。因為伙房的勞教根本就不會做飯,他們之所以能去伙房,那是家人拿錢買關係換來的。一般剛從入所隊分下去的勞教,警察頭頭都會很「關心」的找他們談話,主要詢問勞教家裏的經濟情況,被警察獵取的目標自然也就知道如何去做了。
一大隊雖然是邪惡黑窩的窗口,可嚴重缺水,高高的水塔是個擺設。夏天洗澡簡直就是奢望,能有盆水擦擦就不錯了。冬天洗澡更是活受罪,每組十幾個人,洗澡就十分鐘的時間,幾個人擠一個淋浴噴頭,有的人身上的肥皂還沒來及衝就停水了。沒有水洗臉無關緊要,但是每天的衛生秀是必搞的,地板擦的能照人影。被子疊的方方正正的,不准蓋,那是用來作秀的道具。
6、紀念4.25和平上訪
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那天,大田組十幾個同修相約,為紀念4.25和平上訪兩週年,我們坐在花壇邊一起背誦師父的經文──《論語》。警察發覺後,糾集了小組長、小崗、包夾等勞教,企圖驅散我們,這時,同修們站起來,臂挽著臂圍成一圈,不為惡人所動,堅持背誦經文,那些被警察指使的勞教,為了表現自己,瘋狂的拽、掰、拉、衝、拖、打我們,頓時大院一片騷亂。我們就按師父說的做: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7、抗工反迫害
二零零一年三月底左右,一大隊又被綁架來一個老年大法弟子,鎮江六十二歲的王永新,當時他的老伴也因堅信「真、善、忍」,而被非法關押在江蘇省女子勞教所遭迫害。他到一大隊時間不長,就開始拒絕出工。通過交流大家認識到,我們做好人怎麼做到這兒來了?這不是我們呆的地方,這是迫害我們的黑窩,強體力幹活是他們迫害我們的手段。於是,同修們開始陸續抗工反迫害。
有一次整秧滿田(育稻秧用的田),我那時正在抗工反迫害,到收工的時候,帶工的隊長顧春,有意製造矛盾,以我不報數為由,不讓收工。我據理反問他:出工時我也沒報數,你那時為甚麼不說,不報數大夥就不出工。顧春自知理虧又變損招,要每人說一句法輪功不好的話就收工。我當眾阻止他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下流行為。當時十幾個勞教,只有一個常州姓劉的吸毒犯(可能叫劉一平,外號叫四十五),他說了一句不好的話。現在的許多人,被惡黨系統的洗腦毒害,已不相信因果報應了,但無論信與否,善惡有報都是不變的天理。禍從口出,就因為他說了那句不該說的話,後來有一天夜裏,他和一個南京的吸毒犯互毆,被對手搗的嘴唇外翻,儼然一副豬嘴相,眼睛也變成了特大號熊貓眼,面目皆非。警察對這種事根本就視而不見。有時白天出工,勞教打架,他就把身子扭到一邊去。所以,方強的八大怪,其中的一怪是:方強警察比勞教壞。
還有一次堵壩頭,我抗工不幹,顧春氣急敗壞,就令幾個勞教拖著我去踩堵壩頭的爛泥,我不配合,包夾周家平,為了表現表現多得點獎分,就抱著我往壩下跳。說來有趣,跳下去後三兩下,很有力氣的他卻被搞到我的身子下面去了。我的上衣被他們撕開了很長的口子,渾身弄的都是泥巴。
8、灌食迫害
在那不見天日的黑窩裏,我們反迫害的形式主要是抗工和絕食。我也曾多次絕食反迫害,他們就用鼻飼管從鼻子插管子灌食,灌食也是相當難過的。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在一大隊絕食,他們給灌了幾天,姓吳的獄醫看到抽出來的鼻飼管都帶血,並說反覆插管子時間長了食道就損傷潰瘍了。惡警王飛不聽獄醫勸阻執意灌食,還歹毒的說,要吃也不讓他吃,就給他灌!從他那透過眼鏡,瀉出的邪惡眼光,就知道他要作惡。他親自灌,把管子插進去抽出來,又把管子插進去再抽出來,就這樣反覆有意的折磨我。在我之前,縫紉組有一個同修,灌食的管子插到他肺裏去了,灌的那個同修生命垂危,他們怕擔當責任,又拉到鹽城去搶救。
大概是二零零一年九月底,在三大隊,我們二十八個大法弟子集體絕食,我們反迫害的要求有兩條:一是扯掉櫥窗裏誹謗大法的邪惡標語;二是停止迫害,無條件釋放所有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他們為了逼迫大法弟子停止絕食,竟惡毒的使用電警棍電擊大法弟子。通過同修們共同反迫害,邪惡的標語被除掉了。在其他大隊遭迫害的大法弟子(除專門迫害大法弟子的二大隊外),也都陸續集體絕食反迫害,有力的震懾了邪惡。
9、電擊、關禁閉迫害
電擊、關禁閉都是黑窩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惡手段。禁閉室大概有三四個,禁閉室正面是鋼筋焊的小鐵門,其餘三面是水泥牆,室內有一個約五六十公分寬、不到兩米長、二十公分高的水泥台子,是用來睡覺的,台子上有一張破草蓆,一條骯髒不堪、腥臭熏人的被子。台子旁邊,放一個帶蓋的小塑料桶就是便桶了,大小便都不准出去。台子頂頭到門之間一小塊地方,就是用來罰站的。每天早晨五點開始罰站,而且要按軍姿站,一直要站到夜裏十點。禁閉室有兩個勞教晝夜輪班看守,每天唯一的一次出禁閉室,就是早晨去隔壁的廁所倒便桶。一般關禁閉迫害是十天,這十天不准洗漱,更不准換衣服。
二零零一年六月初,大法弟子王永新,因抗工反迫害,並在一大隊監區院內揭露邪惡。惡警王飛就與黑窩管教科的科長黃建軍暗中勾結,黃建軍親自帶車到一大隊,強行給王永新戴上手銬,把王永新老人拉到嚴管隊。到嚴管隊後,他們用兩根電警棍長時間電擊王永新老人,然後關進僅有3平方米多的禁閉室。這就是邪黨在國際社會上一再高喊的:「中國人權的最好時期」。
二零零一年七月初,我被調到黑窩的七大隊迫害,從各大隊調去的同修集體抗工反迫害。七月九日,拔秧草我不幹,帶工的隊長張×卿,就讓二個包夾看著我,跟在拔秧草的勞教後面走。七大隊的邪黨書記仇正流在外面溜到田邊,看我不拔草,他喝令四個勞教把我按倒在稻田裏。隊長張×卿感到沒有面子,很氣惱。收工的時候,他氣急敗壞的把我推進齊胸深的水渠裏,全身被搞的濕漉漉的。中午,七大隊的中隊長周紅軍和大組長張成功(南京人)、內崗趙貴清(揚州人)兩個勞教,把我架到桑塔納車上送到嚴管隊。我閉眼坐在地上,不一會感覺頭頂很難受,睜眼一看才知道他們在用電警棍電擊。他們野蠻的剝掉我的上衣,用四根長約五十公分、上面繞著粗銅絲的電警棍電擊。管教科的科長黃建軍為發洩私憤,他一人拿兩根電警棍電擊我。另一個南京籍姓楊的惡警,一看便知是個虐待狂,他施虐從受害者的痛苦中而得到滿足。他們不停的電擊我的頭皮(在黑窩裏被強行剃光頭)、前額、眼皮、嘴唇、臉頰、耳朵、脖子、腋窩、前胸、後背等。雖然我沒有被毒蛇咬過,但電擊就像被毒蛇撕咬的一樣難受。
我被關禁閉迫害的第二天,江蘇省勞教局的唐國防,帶著曾在江蘇省女子勞教所遭迫害的三個人,想趁熱打鐵來做「轉化」我的工作,她們偏離了大法後的歪理,可悲又可笑。我很痛心她們,就要與自己苦苦等待的萬古機緣擦肩而過。她們是在酷刑高壓下承受不住了,想尋找解脫,雖然是違心的,那可是莫大的恥辱,也許千萬年的等待因此而付之東流。
接下來的十天裏,每餐只能吃普通勞教的三分之一,每天罰站十七八個小時。由於隔壁就是廁所,臭氣熏天,而且蒼蠅、蚊子很多。蚊子在方強也佔了一大怪:三個蚊子一盤菜。毫不誇張,那蚊子就像小蜻蜓一樣大。到了晚上,它們又像瘋狂的警察一樣叮咬人。沒有蚊帳、蚊香,他們還規定蚊子叮咬不准打蚊子,用這種方式來折磨,人根本就無法睡覺。那麼熱的天,罰站了十天,別說洗澡了,就是臉也不讓洗,也不准刷牙漱口。這就是邪黨自詡的人性化管理。作為一個修煉人,被他們非人的折磨是我的恥辱。然而,當他們不把人當作同類摧殘時,那就是他們無限悲哀的開始。
在我被關禁閉的第三天,七大隊又送來一個反迫害的同修蘇彥,他是武漢人,白白淨淨的大學畢業生,在徐州遭徐州的惡警綁架,從而被迫害到方強勞教所這個黑窩。蘇彥被強迫罰站的第二天,腳、腿開始浮腫,到後來腳腫的連拖鞋也穿不進去了,腿腫的就像穿了棉褲一樣粗。由於他們不讓我們說話,我猜測,他腳、腿都塗抹了紫藥水,可能腳、腿腫的把皮都脹裂開了。
這些僅僅是方強勞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冰山一角。然而,那裏的罪惡還在繼續著。人們喜歡仙鶴,更欣賞它的品格。仙鶴不同於一般的動物,極具靈性。九年了,試問那裏的仙鶴可安好?遺憾的是,美麗依舊的灘塗上,性情高潔的仙鶴越來越少了。因為它們的生性,決定了它們要遠離罪惡的污染。聽仙鶴引頸高亢的鳴叫聲,彷彿在向人們訴說著方強勞教所發生的罪惡;又彷彿在向人們讚頌著大法弟子,那堅信佛法真理、可歌可泣的件件壯舉。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8/10/29/1018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