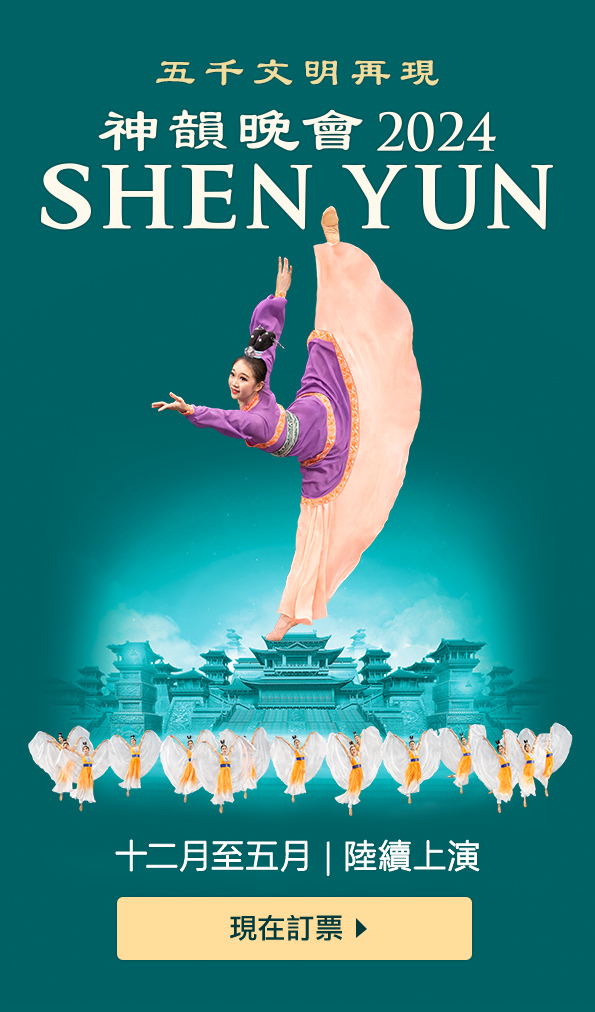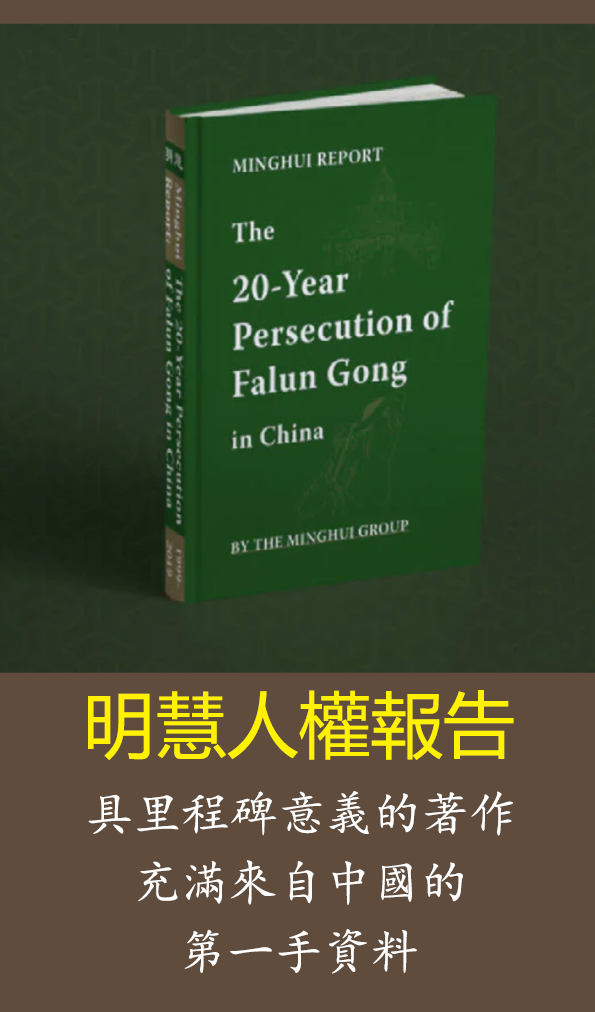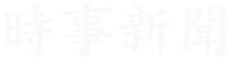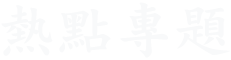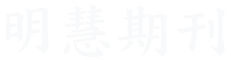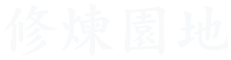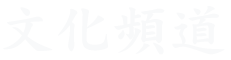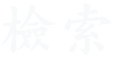我在鶴崗市看守所遭酷刑折磨
半夜11點多鐘,這幫人在我家大搜查,把手機、呼機與複印機等都弄到了市局,這時把我的小妹妹也給抓了來。小妹說家裏被他們弄成了一片廢墟。第二天來了一個姓趙的女局長說了一些誹謗大法的話,說不過我就走了。我要求歸還我的物品,送我們回去,他們說領導開會,等開晚會就送我們回去。直到下午3點多鐘才將我小妹送回去,因為家裏還有孩子上學。後來他們拿來一些材料讓我們簽字、按手印,被我們嚴厲拒絕。
晚上,我們被拉到了看守所,進了看守所才拿出票子讓我們簽字,我們說:「不簽!你們沒有理由拘留我們!」,我們被強行推進了看守所的門裏,惡人們說是奉命行事。隨後,犯人和獄警強行搜身,扒光衣服,連皮鞋都撕開,我的100多元錢和鑰匙、電話卡全被他們沒收。接著被一名犯人押到三號監室。
進號後又被脫衣服強行搜查一遍,然後就是挨打,然後從頭上往身上澆涼水,一盆接一盆地澆,那滋味真是太難受了。然後被逼著到鋪上「碼道」,左右有人卡死,兩腿交叉盤上、手放在膝蓋上、上身挺直、抬頭、不准閉眼睛,背監規。後面四個犯人監視,身體稍有彎曲就是一頓毒打,別人晚上11點就寢,我得下地繼續這樣坐著一動不動,還不時地挨打,他們被教唆得專找心口、後腰、軟肋等地方穿皮鞋踹。有一天他們一邊打我一邊罵大法,他們罵,我就喊:「法輪大法好」,他們罵得聲音越大,我喊的聲音越大,後來他們就不敢罵了。
就這樣他們長時間讓我盤腿坐著不准伸開腿、不准閉眼睛、晝夜不停,我被折磨的精神恍惚。
大約3、4天後,市刑警隊那幫人來了,把我弄到二樓刑訊室,先是那個姓金的隊長說了一大堆歪理,滿嘴髒話,還自稱是老黨員了。見軟的不行,立即變臉,對我一頓毒打,之後又沒完沒了地打罵,我一直靠牆站著,他們說話時,我就站著睡著了。他們喊醒我,我告訴他們,我已經好幾天沒睡覺了,腦子裏甚麼也想不起來。他們說我睡完了覺再談。其實,他們從抄我家那一刻起,我就和他們講真象,他們說他們是機器。他們問我複印機哪裏來的,誰是我的上線,誰是我的下線,跟誰來往,都印了些甚麼,弄哪裏去了等等。我的回答令他們很不滿意,他們惱羞成怒,便幾個人上來把我左手從後腰背過去,右手從肩頭擰過去,兩手銬在一起,因為銬不上,幾個人使勁拉才銬上。他們又把我的衣服掀開,用茶缸蓋的尖往我的肋縫裏插,一邊拎著手銬悠盪著。這樣不分晝夜的折磨拷打、上銬子,我的兩條腿也不好使了。
回號後,號裏的犯人折磨我不讓睡覺,我和他們講真象後,他們告訴我,是管教告訴折磨的,不然,他們要挨「收拾」的。這天,他們又將我從號裏面提出來準備折磨我,我抵制迫害撞到了牆上,他們把我弄到監室坐在地上,有個穿白大衣的人給我縫上了頭頂的大口子。所長李樹林和張建軍給我砸上支棍上了地環。
「支棍」就是一米長的鋼管,兩頭各有一個開口的環,索住雙腳脖子。這樣人的兩腿分開,不能走路,不能蹲。要是戴上棒子更完了,棒子也叫「三環套月」,有兩隻環把手銬到一起,另一隻環銬到支棍的一端。這種東西是看守所給打仗、管不了的犯人用的,犯人都怕這種東西,寧可被打得皮開肉綻,也不戴這種東西。
自從戴上支棍後,每天坐在地上索在地環上,犯人不那樣折磨我了,我可以說話了。他們趁管教不在時,偷偷給我墊上墊子,管教來了再偷偷拿走(因為管教和所長不讓坐墊子)。
在第二看守所砸支棍後,提審更勤了。有時一天,有時一夜。每次被抬來抬去刑訊室,因支棍支著腿,等到了地方兩腿被支棍別的就不會動了。可他們讓我站著,彎腰、兩腿抻直,然後用力砸我的大腿,用皮鞋踢,肉就離骨了,就站不起來了,然後又是幾個人拽著兩隻手一上一下扭到背後銬上,這回更遭罪了,戴支棍坐在地上,後邊還用一把椅子卡住,接著就是「數肋條」折磨我半夜,留下一個人看著我,我聽見有人痛苦地大叫聲,不知道又折磨誰去了。
我就這樣雙腳上著支棍,雙手大背銬著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那種痛苦就想趕快死掉,我叫看我的人趕緊給我解開,他說沒有鑰匙,直到天亮了才給我解開銬子,可是由於銬的時間過長,銬子是幾個人使勁拉才銬上的,所以怎麼也打不開,此時,他們也不管我的死活了,幾個人把我按在地上,用力把胳膊往一起對,最後終於打開了,他們累得呼呼直喘。打開後手拿不下來了,幾個月後手才漸漸有知覺。他們聲稱:「你不說,就到一看守所弄幾個死刑犯來,我們也不問你了,你想說也不聽了,叫死刑犯整你死!」早上六點被他們抬回了監舍。
2002年6月我又被批捕轉到鶴崗市第一看守所關押,之後鶴崗市工農區法院強行判了我10年徒刑,於2003年9月1日送香蘭集訓隊,9月8日又被集訓隊送到了佳木斯監獄。
這期間,我的小妹妹劉玉霞也被他們抓到了看守所,遭到了同樣的迫害,又被判了三年教養送到了哈爾濱。孩子無人照顧(離異,孩子歸她撫養)。大妹妹劉玉紅不知被他們用了甚麼手段,在2002年8月迫害死了。我70歲的老父親因不堪忍受公安、街道、區裏、辦事處等部門的不斷騷擾,於2002年被迫離開了老家,現在只有一個七旬的老母照顧小妹的孩子和偏癱的弟弟。
請鶴崗市法輪功學員提供有關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