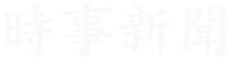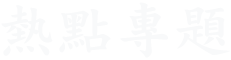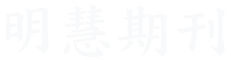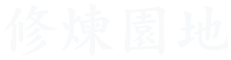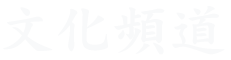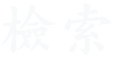護法,在「7.20」(一)
——我的所見、所聞、所感
童年的我,非常的善良,上小學時聽語文老師講雷鋒的故事,為小雷峰的悲慘童年而悲痛難抑,痛哭了整整半堂課。
時光流逝,童貞漸失。在社會這個大染缸中隨波逐流,越來越體會到做個好人的艱難。我一直在探索著人生的真諦。學校裏學到生物學、進化論,講到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那說白了,生物界不就是弱肉強食嗎?當時覺得大概人就是這種東西進化來的,所以也講個勝者王侯,敗者賊寇。
古代的岳飛,現代的雷鋒等等,為何不是慘死,就是英年早逝,做好人真的不得好報嗎?從絕對唯物論上講,人死後甚麼都不存在了,沒有鬼也沒有神,那老天也不可能有眼的。這個世界真的是無情地、機械化地在運轉著客觀規律嗎?
我深知客觀規律之不可違背。然而在狠起心來實施成王敗寇律時,我善良的本性卻又承受著深深的挫傷。我欲哭無淚,無奈啊……
在這種彷徨中,我變得越來越有城府,思想越來越複雜。後來到卡拉OK去打工,從服務生到領班到經理,幾年間做過幾家酒店。期間幾乎見識到了人性的一切醜惡,以及從各種各樣有錢、沒錢,有勢、沒勢,有權、沒權的人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的心變得越來越狠。同時發現,不光是服務行業,而是整個社會道德都在淪喪。
就在這種最危險的時刻,甚至可以說我的一隻腳已踏向萬丈深淵的時候,一個偶然間我遇到了一本叫《轉法輪》的書。
那一天,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我得法了,我明白了宇宙的真理,我明白了宇宙的燦爛,我體驗到了回歸真、善、忍的生命是多麼的自由,我甚至好像聽到了發自我生命本源的歡呼!我得法了!!!
我得法了,明白了無私無我的輝煌,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宇宙的燦爛,明白了師尊的慈悲(當然這種明白是在我的層次和境界中的明白)。明白了法正乾坤的意義,明白了《苦度》中說的「危難來前駕法船,億萬艱險重重攔,支離破碎載乾坤,一夢萬年終靠岸。」
﹒ 護法
我讀過和聽過許多大法弟子的修煉故事,看過「明慧」網上的很多好文章,為大法弟子們的偉大而感歎,為師尊的慈悲承受而淚下。我悟到,作為一個偉大的大法弟子能夠為了維護「真、善、忍」大法而付出一切,對於一個產生於「真、善、忍」的偉大生命來講,是他們的本質和本分。
又一個「7.20」到來,我理所當然地走向了天安門廣場。廣場上警衛很多,我找個地方一坐,開始打手印,到加持神通不到一分鐘吧,就有一武警到我面前,先是一個立正,接著一個敬禮說:「請站起來。」我沒有動,他就又來了一遍。我知道這種「文明」的舉動是做給旁人看的。如果真的那麼文明,我們就不必為「真、善、忍」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就不會有大法弟子們被折磨,就不會有弟子們被打殘,更不會有追求「真、善、忍」境界的弟子們被活活打到死。
緊接著一群便衣圍住了我,看我還是不動,其中一個一腳踢向我盤著的腿。我被拉起來,便衣們緊張地問我哪裏人、身份證哪?我說沒帶身份證,也不想說哪裏來的。我知道說出來就要送回當地,並施以各種各樣的罰款並坐牢,家中也不得安寧。我覺得把錢給那些迫害法的人會助紂為虐,把矛盾激化到家庭內部會變相地成全了迫害法的人,所以根本就沒想帶身份證。
一個便衣說:「還沒聽說過有不說的。」我明白他的言外之意,平靜地看著他說:「我想試一試。」另一個便衣說:「小年輕的,學點甚麼不好,為啥就不學好呢?」我轉過去對他說:「我本是個很壞的人,就是學這個法學好的。」
這時警車在廣場上開過來、開過去抓人、裝人,我想周圍可能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們為甚麼請願,就想喊出來告知世人,但是人的一面還有甚麼東西擋著我,讓我好像是不好意思開口。我一發現就知道這個東西必須破除,而且警察和便衣大概最希望的就是安安靜靜地把我們裝上車拉走,警車向我開來的時候,我向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喊:「法-輪-大-法」,便衣們慌了,衝過來捂我的嘴,我扭頭掙開,再次喊出來,這時警車到了,裏面坐滿了大法弟子,我向他們雙手合十。
車開到派出所,(好像是前門派出所)我們背靠牆站成一排,我在最前面,面前的警察,斜靠著椅子,把兩隻腳高高地架到桌子上,問我哪來的,叫甚麼?我說我不想說。警察說:「甚麼叫XX不想說啊?」我說:「我學法輪功學得很差,但學法以前總說髒話,學法以後就再也不說了。」那位警察一下子就被噎住了,頓了一下,把腳從桌上放下來。接著是要求把東西都拿出來,警察翻看我的錢夾,從裏面拿出一張紙來讀到:「《致公安部門的有緣人》,行啊,這張紙我留著慢慢看。」我說:「好啊。」我出發前見到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好,就準備了一張帶在身上。
到了後院,裏面已經坐著很多大法弟子,有的在交流,有的在背師父的新經文。不一會兒就裝車轉移。大客車兩邊椅子上坐了七、八個警察,大法弟子們坐在中間。一路上,我們不停地背經文和《洪吟》。警察要我們停止,打了幾下無效,後來為了「殺一儆百」 ,拎一位弟子到前面摁到地上連踢帶打。我們紛紛喊出:「不許打人!」我站起來往前趟,喊到:「不許打人!」警察們回過頭來看,好像是打人的效果出乎意料。我又說了一遍:「不許打人!」一個警察喊坐下。他們不打了,我們也就坐下了,大家繼續背。我旁邊有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同修,背得很流利,純真可愛。
車到了一個地方,下車換吉普車,這時我看到車上下來一位八、九歲的小女孩同修,背上還背著書包。
到了一個北京郊區的派出所,警察翻來覆去要求我說出地址姓名,我說:「只要是我說出的都是真話,我不想說的我不說,我是來護法的,我覺得我說出姓名地址對護法沒有好處,只有壞處。」
我還講起一個澳洲弟子的經歷,這位澳洲弟子在北京和同修交流時被非法拘捕,帶上手銬提審時警察問到:「你來北京都住在誰家呀,你學真善忍就得說實話呀。」澳洲弟子說:「真、善、忍不還有個善字嗎?真和善是統一的。」他舉了舉手銬說:「你看你們對我都是這個樣,我把他告訴給你,你們對他能甚麼樣啊?這是真嗎?更談不上善了。」
警察問話經常兜圈子,比如問:「以前來過北京嗎?」我說:「來過幾次」。說完之後馬上反應過來了:他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判斷我是不是北京人。(待續)